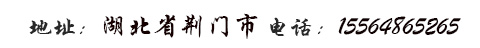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 凌晨三点,我睡不着。窗外淅淅沥沥下着雨,雨滴打在窗外的树叶上。过了一会,雨变得大起来,我能听见水流卷着垃圾冲入下水道的声音。风从百叶窗的缝隙里刮进来,带有一丝凉意。我记不清这是入夏以来第几次失眠了,睡前我还喝了一杯牛奶,试图借助它来消解我敏感亢奋的神经带来的精神头——显然失败了。不管怎么样,我不会吃安眠药的,一粒也不。我担心我会就此上瘾,对药物产生依赖。我不希望对哪样东西产生长久性的依赖,哪怕是人呢,更别提药物了。我不知道周伟在干嘛,晚上我们分开后就没联系过,他或许已经早早入睡。我脑子里想着他对我说过的事。第一件事,关于一个女孩。第二件事,还是关于一个女孩,不过是另外一个。他是怎么对我说这几件事的呢?“我遇到了一些麻烦。”周伟说,这是他在跟我讲第一件事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那时我在家,锅里正在煮饭。下午六点左右,天阴沉沉的,还刮起了风,树叶呼呼作响,光线很快便黯淡下去。除了做饭,我手头还有一大堆活要处理。房间的地板上堆满了书,两边货架上也都是书,数不清的、印有不同语言的各式各样的书籍。我一边把订单打印出来,挑选顾客需要的书,一边将剩下的书分门别类,整理上架。我把需要发出去的都包装好,然后塞进快递袋中,等着快递员上门取走。这就是我的工作。订单中偶尔有几本冷门书籍,我这里没有,就得去求助二手市场。有时候看着这些五花八门的书,我会想,对方是什么人?干的什么工作?需要这些书籍有什么用呢?更多时候,我只是机械重复地忙碌着,并不会想那么多。我闻到了一股饭糊味,连忙冲进厨房把煤气关掉,为时未晚,锅底只糊了一点。然后我回去继续忙手头的事。周伟打电话过来,约我出来聊聊,我把包裹堆在房间角落,就和他出去了。他给我讲的第一件事就是关于这个女孩的,我问他她叫什么名字?周怡,他说。他俩同一个姓,说不定几百年前还是同一家。我说别扯这么远,没用。他说都是同一个车间的工人,周伟负责组件,周怡负责检验。有一天,车间里送来一批需要加工的机床零件,周伟发现其中一个有瑕疵,就去检验科找负责人。检验科很小,在楼梯拐角处,门上挂着一个木牌,“检验科”三个蝇头小楷,字迹清秀。推门进去,一道简易门将房间隔成两个区域,前面是工作台,后面是休息室。工作台是一张红木桌子,上面摆着一个台历和一只笔筒。那里没人,他就往后走。拉开简易门,一张钢架床放置在角落,四脚涂了蓝漆,床单也是蓝色的,床上放了一床白被褥,医院的病床。一个女孩从床上跳下来,慌忙用手抚平衣服上的褶皱,“你是干嘛的?”女孩问,周伟并不认识这个女孩,她看上去很年轻,皮肤白皙。周伟把零件拿给她看。她把头发扎成一个髻子,露出细长雪白的后颈。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根钢笔,“明白了,跟我来吧。”她说。周伟当时觉得,这个女孩与众不同。和厂房里紧张忙碌的工作环境相比,她显得如此恬然,语气也极为平静,是他喜欢的那种类型。后来周伟才知道,原先负责检验的阿姨已经退休了,眼前这位是她的小女儿,“我叫周怡,负责检验,咱们是一个车间的。”女孩告诉她。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之后,周伟对她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况且他们都是单身,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两个人心里肯定考虑了很多东西。他们开始频繁交流,互送礼物,下班以后经常待在一起,周伟有时候会在周末找她。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关系变得暧昧,模糊不清。但我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没人跟我提起过。周伟说的麻烦指的是什么?他告诉我,有一次他俩晚上出去吃饭,周伟点了一份牛肉汤,汤很辣,很咸。周怡不知道,用勺子喝了一口,接着又喝了一口,头上立马冒出了汗,嘴巴发红,脸上的颜色先是变成深红,然后逐渐发白。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她用手按住胸口,身体不停发抖。“出什么事了?”周伟问她。周怡已经说不出话来,头一歪,直直倒在椅子上,手里的汤勺跌落在地,摔得粉碎。周伟见状大惊失色,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脑子里闪过荒唐的念头——厨师在饭菜里下毒。但这是不可能的,他立刻清醒过来。餐厅里的客人渐渐围拢过来,在他们身后站成一圈。“你们让开点。”周伟说。人群打开一个缺口,他赶紧背着周怡上了他的摩托车。车子发动,他一手扶着握把,另一只手拉住周怡的胳膊。周怡靠在他的肩膀上,头发垂下来遮住脸颊。他感到她的脉搏在跳动,速度快于常人。他感到害怕,身体的血直往头上涌。他加快速度,医院。“心脏病犯了,情况还好。”医生递给他一张片子,“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饮食切忌高油高盐,她没跟你说过吗?”周伟只记得她对他说过她的身体不太好,但没有说过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周伟说。“那你现在记住。对了,你是她什么人?”医生警觉地看着他。周伟愣了一下。他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当时问自己,他是她什么人?对周怡来说,她又是他什么人?他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神情涣散,双手放在腿上,直到夜色将他笼罩。隔着病房的玻璃,他看到周怡在床上睡着了,鼻子插着呼吸管,输液瓶挂在墙上,药水正源源不断地输入静脉。他放慢脚步,走进去待了一会,然后轻轻走了出来。他下楼找了一家商店,给周怡买了一些水果,在医院楼下,他抽了一根烟,对面高楼上的霓虹灯闪烁不停,灯光照在脸上,阴影与光线交替流转,魅艳动人。有那么一瞬间,他分不清这一切是否是真实的,自己为什么会站在这里,叫周怡的女孩为什么躺在病床上,对他来说,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好似命运开的玩笑。他们本应该愉快度过这一天,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像是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起床,洗漱,然后去工作。这件事情好似当头一棒,将美好的滋味击得粉碎,情况急转直下,问题变得棘手起来。关键在于,它没办法像别的事情一样一劳永逸地解决,不管对谁来说,这件事情都将伴随终生。如果只是一次单纯的感冒发烧呢,周伟希望她正在经历这个,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治愈,而不是一辈子跟一种叫做先天性心脏病的对手做抗争。他正在经历人生道路的分叉,等待有人将他解脱出来。周怡恢复好以后,他俩还是像平时那样保持联系。他俩的感情(如果真实存在的话),会不会因为这件事而受到影响?他问我,“如果是你,怎么选择?”我想了一会儿,说,“我说实话,你不要怪我。如果事情是你说的这样,我觉得就此止步,对双方都好。”我知道我说这话太过自私,但是我清楚,任由其发展下去,事情早晚会走向终点。决定权不在周伟手上。感情上的事,时间越长,痛苦就越深。周伟说他知道,他只是没想好怎么对她说。或许可以一步一步慢慢来。他问我有什么建议。我对他说,这种事情好比下棋,有时候旁观者不一定清,当局者不一定迷。你俩已经坐在棋盘上博弈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手里拿着棋子,心里亮堂的跟明镜似的。你问我怎么做没用,我只是个局外人。所以说,世事由人,这事得你亲自解决。那天晚上我们喝了点酒,他给我讲完这件事,又给我倒了一杯。接着我俩去了章凡家。夜色如水,路上十分安静,街道上没什么人,能听见我俩的脚步声。安静的环境能让人想起很多事情。章凡在家刷锅洗碗,水池里摞了一堆碗碟,黄色的汤汁上面漂浮着油星,那是中午吃饭剩下的餐具。我问他晚上吃饭了没,他说没有。周伟想带他出去吃,他拒绝了。他从冰箱里拿出一袋冷冻排骨,拎进厨房,然后扔到案板上。排骨冒着森森白气,袋子下面是一块血水冻成的冰碴。他问我会不会做排骨汤,我说当然,以前在家经常做。我想起了我的上一任女朋友,有一年冬天她骑车摔着了,挺严重的,车把都摔断了,胳膊和左腿上打了石膏,在家休养了一个多月。那段时间我经常给她熬排骨汤喝,她也爱喝。喝腻了,就换种口味。我往汤里搁红枣和枸杞,她不喜欢那种味道,说红枣太甜了,喝的发腻。后来我换成了铁棍山药,她也不喜欢。我说这不是你家乡特产吗,你怎么不爱喝呢?我打趣说,说明你不爱自己的家乡。她想了想,说,也许是你没买对,那不是正宗的铁棍山药,你买到假货了。我说,有可能吧。后来我还做过山楂味的,梨子味的,有一次我还往里面放了一根老参,是从我爹房间里偷出来的,他想泡酒,但一直没舍得。她喝完直流鼻血,说我是不是傻,又问我,要是被我爹发现了怎么办?我想了想说,怕啥,不就一截树根嘛,发现不了的。然后我把它洗干净晾干,又给偷偷放了回去。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确切来说,只是关于那段日子的记忆,这些记忆日渐遥远,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有一段时间我做梦还会经常梦到,后来就梦不到了。我把排骨放进水池里解冻,烧了一锅水,把排骨焯水,撇去浮沫。章凡问我,做排骨汤都需要什么材料。我说葱姜、八角、花椒、盐和鸡精,还有白萝卜,莲藕。对了,我说,再来点白酒去腥。我本来还想说放一些红枣和枸杞的,但我没说。章凡猫着腰在橱柜里找了一圈,除了香料和半瓶白酒,其他配菜一样也没找到。他说家里没有了,咱俩出去买吧。周伟坐在沙发上,问到底怎么回事,大半夜的做什么排骨汤?超市都关门了。我看了看表,夜里九点半,确实不早了。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也有些饿了。我说,咱不做排骨汤了,做点别的吃。我走到厨房,打开燃气灶,起锅烧了一些油,然后把排骨擦洗干净,剁成小块,裹上一圈粉芡,放进油锅里煎,排骨滋滋冒泡,颜色变得金黄。趁这会儿功夫,我又调了碗料汁倒进去,调成中小火,烧了一锅红烧排骨。盘子端出来,香气扑鼻。灯光底下,排骨颜色鲜亮,令人垂涎。我们把没用上的白酒拿出来倒上,三个人边聊边吃。不久,一盘排骨啃得精光。周伟喝的有些醉,抱着章凡讲故事,他俩躺在沙发上,酒酣耳热,絮絮叨叨。我离得远,一个字也没听清。我把盘子端进厨房,在水龙头底下冲了冲,然后回到他俩身边躺下。我枕着章凡的腿,听周伟讲下面这个故事。大概五六年前,周伟那会儿还在上高中。学校在县里,离家挺远的,乘车要一个多钟头。被原来的学校开除以后,他妈就把他送到这里,说要让他好好反省。好好反省,反省什么呢?周伟说,他什么也没做错,他妈却把他送到这里。班里一个人都不认识,也找不到人说话,净是一群怪胎。班主任给他分了一个同桌,是个女孩,她挺奇怪的,平常不跟人说话,也不交流,像个哑巴。周伟说,我一直以为她是个哑巴,后来有一天她找我借钢笔来着,才知道她原来不是哑巴,就是不爱说话而已。他俩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就这么过了一个学期。有一次周伟返校,听见班里闹闹攘攘的,他跑过去,发现是几个人在打架。他给我们讲,打架的那两帮人特凶悍,逮着什么抡什么,而且都是照着要害。打斗中,有一帮人占了下风,被人追着打,有一个小个子落了单,站在一旁战战兢兢,结果被一个胖子猛踹了一顿。周伟讲义气,看不得有人受欺负,就想上去打抱不平。这时周伟感到有人从背后拉住他,他回头看,发现是他的同桌,那个女孩拉着他的衣服,嘴唇紧咬,眼神柔弱,不住地摇头,仿佛在乞求他不要过去。周伟气血上头,想都没想,一把推开她就冲了上去。这就是周伟第二次被学校开除的经过,他替人出头,后来被同伴指认为主犯。对方在混战中用铁板凳砸中了他的腰,他则用一把小铲子拍了对方的脑袋,给他开了瓢。“小铲子是哪来的?”我问他,我对这种细节很感兴趣。“不知道,”周伟说,“可能是从家带的,我记得那个周末我回家帮我妈种花来着。放在裤子里忘了拿出来。”“然后呢?”章凡说,“接着说呀。”周伟继续讲下去。被开除的那天,天上下着小雨,学生们都在教室里上课。他和他妈背着行李,一前一后走在校园里。气氛安静得吓人,他不敢回头看他妈的目光,其实那里面已经没有了埋怨,只剩下无奈。在校门口,他回头张望这个他只呆了几个月的学校,忽然看到远处的雨幕里有一个身影,谁会站在那里呢?他看不清,以为是班主任,或者别的什么老师。他妈也回头看,说是一个女孩,低个子,长头发。他立即明白了,那是他的同桌,那个拉住他衣服的女孩。他想回去找她,跟她说点什么,但是她走开了。周伟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周伟被送回了浙北老家,那是一片水乡,稻田里经常看到有人捉鱼摸虾,还有老人赤脚站在水田里插秧。周伟的腰伤没好彻底,阴雨天经常腰痛。医生要他勤晒太阳,于是,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他总是坐在村口晒太阳,像一个老人那样。按照老家的风俗,一个人如果不上学了,就应该找个对象早早结婚,成家立业。媒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一来二去,两个人就熟了。其实他俩早就见过,有一次周伟出来晒太阳,那女孩路过,眼睛看着他,走出去没几步,突然捂住嘴笑出声来。崔雯,周伟告诉我们,那女孩叫崔雯。后来周伟不再是一个人晒太阳,他身边有了崔雯。崔雯帮忙照顾他,给他买药,做饭。腰伤好了以后,他带她回到了城市里。家里给他们买了一所房子,他俩就住在里面。除了没有举办婚礼,他们做了所有他们想做的事情。崔雯找了个销售的工作,周伟继续上学,他考上了一所职业学校,打算毕业以后去做装配。没课的时候,他就和师傅外出干活。到了假期,周伟会带着她出去旅游,国内游遍了,就去东南亚,欧洲。直到周伟毕业,他们一同生活了三年时间。周伟想起这段日子,又爱又恨。前两年如胶似漆,到后来的貌合神离,分崩离析。他看着他们一步步贴近,彼此融入共同的生活,又看着两人之间的感情出现裂缝,他试图弥补,然而缝隙越来越大,变成深不见底的黑洞,将二人彻底撕裂。“我不知道一个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周伟说。我知道他说的是崔雯。他说,那段日子,他亲眼看着她变成另外一个人,爱慕虚荣,攀比,酗酒成性。曾经温柔贤惠的女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染上酒瘾以后,她就几乎不再在家吃饭,每天下班后喝的醉醺醺的,倒在自家客厅地板上呼呼大睡。到了后半夜,她会准时醒来,约上三五好友继续出入酒吧。一开始偶尔夜不归宿,后来变成整宿整宿不回家。周伟说,他不止一次接到陌生人打来的电话,有时候是崔雯的朋友,有时候是酒吧服务员,还有几次是警察。他们告诉他,你的老婆喝醉了,快来把她接走。或者是,您妻子醉得有些厉害,您能不能把她接走,顺便把账单结掉?他一周会接到三四次类似的电话。周伟忍无可忍,他给她下了最后通牒。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两个人都喝醉了,崔雯抱着他痛哭,她求他不要离开他,她会改过自新。周伟也承认他在某些事情上做的不好。“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她问他。他们抱在一起,眼含热泪,亲吻对方。周伟希望,经过这一次,生活会慢慢变好。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崔雯重复起了过去的生活,她从酒徒那里学到技巧,懂得如何撒谎隐瞒对方,学会把账单撕掉,服用解酒药,并把酒瓶隐藏起来。周伟一度以为崔雯真的改过自新了,然而种种迹象都在表明,崔雯毫无悔改之意,并在谎言遮掩下更加肆无忌惮。识破崔雯的伎俩之后,周伟懊恼自己怎么会轻信对方的谎话。几番回合较量,周伟感到筋疲力竭,他无力再和对方玩猫鼠游戏,干脆断了感情一了百了。周伟说,那天凌晨,他睡不着。崔雯还没有回来,他试着给她打电话,没有任何回应。周伟爬起来,走到她的房间,那时候他们已经不住在同一个房间了。他闻到房间里弥漫的酒精和香水气味,看着空荡荡的床,想到她又一次彻夜未归。周伟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怒了,他要全部释放出来。他挥起拳头狠狠砸向墙壁,直到墙壁上出现斑斑血迹,手指像骨折了那样痛。他有一个疯狂的想法,等她回来,他要把这些雨点般的拳头全部砸在她的脸上,但是他没这么干。他坐在床上呆了一会儿,乌云正在散去,太阳缓缓露出一角。他花了点时间,翻箱倒柜,把她的所有东西全部塞进一个行李箱里,然后把它扔到家门口。他势必要将她的所有痕迹全部清理出去。他点了支烟,坐在客厅等她回来。他听到楼梯传来脚步声,脚步声在门口停了一下,她走进来,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周伟拎着她的胳膊,朝门外走去。她踉踉跄跄,摔倒在门口,她看着周伟,泪水从眼角涌出。周伟说,票买好了,我送你回去。他拿上摩托车钥匙,在受伤的手上戴上手套,提着行李箱下了楼。他将她送到车站大厅,天蒙蒙亮,车站广场上聚集了一些人。他从钱包里拿出一些现金递给她,你走吧。他说。说完他就骑车回去了。顶着寒风,他感到脸上冰冰凉凉,用手擦也擦不干净,像有什么东西粘在了脸上。“那辆摩托车,”周伟说,“我送她走的时候骑的车子,是崔雯和我一起买的。过去她支持我的爱好,还给了我一笔钱。”他说,“不过已经是过去了。”从车站回来以后,他去了父母家一趟,但他没对他们讲这些。他只是说他经常失眠,打算搬出去住一段时间,暂时换个环境。他回家收拾东西,路过她的房间,那个女人带着他的一部分生活走了,他亲手送走了她。周伟觉得自己的心也空了一部分,这些年来,他一直在等待谁来填补这块空白。他记得崔雯后来打电话给他,两个人只是寒暄了一下。关于过去,什么也没有提。崔雯说她在老家换了一份别的工作,还跟朋友合伙开了一间商店。她问他最近怎么样,周伟说一切还好,他毕业之后没有去干装配,而是进工厂做起了组件。离开她以后,生活正在慢慢走向正轨,他感觉到了。但是他没有说这个,只是说还好。“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崔雯问他。他沉默了一会,电话那头传来忙音,她挂断了电话。我问他后来呢,他说没了,能想到的就是这些。他说他原本不会想起这些东西来,只是因为谈起了过去,这些记忆才被重新唤醒。他已经记不清她的长相和声音了。然后他问我,能不能用我的手机帮他打个电话,我说给谁?他说崔雯,他想听听她的声音。我说好,我有办法跟她聊聊。我可以假装是外卖员,然后告诉她自己拨错了电话。我打开拨号键,问他电话号码是多少,他想了一会,说,我记不得了。我让他再好好想想,我知道他不会的,有些东西是刻在脑子里忘不掉的。我也尝试着回忆一串熟悉的电话号码,我曾经以为自己早就把它忘了,可是每当有这个念头时,记忆就像两根电线一样顺利地接通在一起,那串号码我几乎可以倒背如流。那是我上一任女朋友的电话,我们曾经打过无数次电话,所有心事都在电话里一一倾诉。但是现在,我觉得我最好不要想这些东西。接着,周伟说出了一串电话号码,我问他是不是真的要拨出去,他拿过手机,一字一字将号码输进去,他看了一会,又将其一一删除,把手机还给我。午夜时分,我们离开章凡家。外面下起了雨,我让周伟注意安全,他说他会的。我躺在床上,听着自己的呼吸与心跳。此刻我的脑子里想着很多东西,但是无法将它们说出来。雨声停止的时候,我终于睡着了。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就站在她家楼下,那时候她还是我的女朋友,我给她做饭,陪她做任何事情。我抬头望着她的窗户,她的身影不时出现在窗子后面,但是她不知道我在楼下,也许她知道,我潜意识是这么认为的。我迫切希望我能见到她,我希望她会走下楼来见我。但是等了许久,我还是没有看到她的身影。这时有一股力量将我向后拉扯,我感到自己不停向后退去,我在慢慢远离她。然后我突然惊醒,醒来以后,发现满头都是汗。我想,我肯定是脑子坏掉了,我为什么要站在那个地方,去等待一个已经不属于我的人,祈求她看我一眼?我们的生活,就像我与那扇窗户的距离,越来越远,直到彼此都看不见。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zhangzx.com/xzjj/12575.html
- 上一篇文章: 忆家乡的酸枣树
- 下一篇文章: 怎样购买感冒药不被营业员忽悠,小编来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