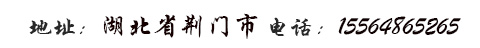失而复得倪柝声与张品蕙的结婚经过
|
擅长临床白癜风研究的专家 https://m-mip.39.net/disease/mipso_5503607.html 倪的得救与二人的分手 出生于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也受过优秀的教育,在学习与组织方面都很有才华,其家庭在福州上层社会亦有广泛人脉,又逢社会运动不断,爱国浪潮高涨。年轻时代的倪柝声积极参与五四运动,组织罢课游行,成为学校风云人物,似乎有大好前途。学校的同学也能见证他是“何等不得了的学生,也是何等了不得的人物”。 然而,这一切看似有前景的计划在倪氏信主之后有了很大改变。年2月,倪柝声和母亲去福州天安堂听余慈度讲道,深受感动。两个月后,年4月29日晚,倪柝声在祷告中决志不惜一切代价委身于信仰。虽然那时他有不少梦想与计划,也有出色的才华与能力,但为信仰的缘故决定“断送前途”。他说,“那时我是个青年人,有许多好梦,有许多计划,为自己的前途设想,以为自己的断案是好的。自己若在世界打拼的话,很可能会有大成就”,但在得救以后,他原来的打算“都空了,都完了,前途都断送了”。[1] 得救之后,倪柝声便迫不及待地向张品蕙传福音,急切希望她也相信基督,但是传福音的结果并不理想。倪柝声说,“当我向她提到主耶稣的事,并劝她相信时,她把我当作笑柄。”这样的结果使他十分难受,不禁思想“我对她的关系到底是如何呢?说起爱来,我是爱她,但我让她笑我所信的主。”同时倪氏思考“到底是主在我心中有地位呢?或是她在我心中有地位呢?”[2] 这种担忧使倪柝声颇为困扰,无法安心,尤其在他读到诗篇第73篇后,这种感觉更为强烈。倪柝声说,“有一日要去讲道前,打开圣经要找题目,顺就翻到诗篇第七十三篇二十五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读后就对自己说,“诗篇的作者能说这话,但我是不能的。”他心里仿佛有一种声音在说,“这就是你的拦阻。” 虽然倪柝声曾表示愿意放下恋情,但在心中仍然无法释怀。他在祷告中痛苦地求神在这件事上给他自由,他“对神讲道,要神忍耐,求神先给我力量,以后我才放下她,请神慢一点来对付这事。甚至“打算到边荒的西藏去布道,或者能使神不向我题要放下我所爱之人的事。”但是“无论怎样祷告都通不过,在校亦无心读书,追求灵命又得不着。”因此,极其难过。 大约过了两周时间,直到年2月13日晚,倪柝声完全奉献自己,祷告说:“主啊!我从今以后,实不以我自己为已有。我为祢的缘故,甘愿舍弃一切。生也好,死也好,我都是祢的人,主啊!除祢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祢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主的爱,是永远的,是到底的。所以我也应该爱主到底,到永远。”[3]他在祷告后大声宣告说,“放下她吧!永非我的人!” 这样宣告之后,倪柝声终于释怀。他说:“那一天,我看世界变小了,好像只有我一人腾云驾雾于天上。我得救的那一夜,我的罪担全脱落,但放下我所爱的人那一天我的心中一点霸占的东西都没有了。”[4]同时,他把与张品蕙之间所有来往的信件都焚烧了,并在日记上写道:“基督是我的爱人”。又另外写封信到北平,告诉张品蕙说,他们二人的关系到此为止。[5] 在经过这样一番彻底的了断后,倪柝声写了一首诗歌《主爱长阔高深》(大本诗歌第首),表达他的心境: 主爱长阔高深,实在不能推测; 不然,像我这样罪人,怎能满被恩泽。我主出了重价,买我回来归祂; 我今愿意背十字架,忠心一路跟祂。 我今撇下一切,为要得着基督; 生也、死也,想都不屑,有何使我回顾? 亲友、欲好、利名,于我夫复何用? 恩主为我变作苦贫,我今为主亦穷。 我爱我的救主,我求祂的称是; 为祂之故,安逸变苦,利益变为损失!你是我的安慰,我的恩主耶稣! 除你之外,在天何归?在地何所爱慕?艰苦、反对、飘零,我今一起不理; 只求我主用你爱情, 绕我灵、魂、身体。 主啊,我今求你,施恩引导小子, 立在我旁,常加我力,过此黑暗罪世。撒但、世界、肉体,时常试探、欺凌;你若不加小子能力,恐将贻羞你名! 现今时候不多,求主使我脱尘; 你一再来,我即唱说:阿利路亚!阿们![6] 一年后,倪柝声回忆此事时说到:“去年读经至此,每不能释然。盖余心坎内,实不能发出此语也(指诗七十三25)。盖余爱友之心切,虽甚爱主,究欲兼爱。主数欲余顺之而舍弃一切,余竟不能。后主示余以为苟余欲为主所大用,则必当完全顺服,否则圣灵不能充满。余与主商,以为爱人亦是佳事。主奈何欲使余清冷了此一世哉。主以为是爱非从主而来,乃世上之爱情也。此后自思每觉主曾为余舍弃一切,今余虽为主舍一切,然而余之一切尚不能较吾主一切之万一也。“主啊!求祢保守我献上的心。”[7] 尽管多年后,倪氏说“年轻人在陷入感情后很难出得来”,但倪氏在与张品蕙断绝关系后的周年之际,表明虽然自己为主舍一切,但和“主所舍弃的一切”而言,自己所放下的仅仅是微不足道。从中可见,倪氏在信仰上的热忱与教会活动的忙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自己情感受挫带来的失落。 在与张品蕙断绝关系之后,倪柝声便全心全意投入教会工作。年秋,尚是学生的倪柝声便为传教十分火热。他不断向同学传福音,并天天在日记中为同学祷告。同时,他与其他几位弟兄在福州城里大街小巷请人听福音。年,倪柝声在三一学院的最后一年,学校受罢课影响而关门。那时,倪柝声与几位弟兄每天有三次祷告会,一次在清晨,两次在晚上,同时在福州城里传福音。 年1月,倪柝声邀请南京李渊如到福州十二间排讲道两周。李渊如离开后,倪柝声又接着连续讲道约一个多月。他说,那时我们“热切地传福音,盼望别人也一样的得救。我们有几十个人常常穿上福音背心,前面写的是‘你要死’,后面写的是‘信耶稣得救’拿着福音旗子,唱着诗,游行各处,吸引人来听福音……地方不够大,椅凳不够多,所以聚会的时候,从客堂到厨房都坐人,椅凳由赴会的人自己带。我们曾看见人带凳子到广场看戏,今天竟然看见人带凳子来听福音。我们为着节省的缘故,厨房、客堂、大门,只用一盏电灯,把花线接得长长的,拉到前、拉到后地照亮人。我们是打穷算盘而盼望多救灵魂,结果那一次救了好几百人”。[8]这些举措在福州城里算是一大创举,功效显著,约有数百人得救,于是倪氏开始组织在王连俊家里的庭院聚会。由于刚刚得救的青年众多,倪柝声不得不花很多时间举办查经祷告聚会,帮助他们在灵命上成长。 与此同时,倪氏开始着手办《复兴报》,并且免费分发给各地需要的基督徒。由于该报深受读者喜欢,销量大好,虽然当时每期的印刷数量为份,但是常常不够,各地经常来函要求补寄。[9]毫无疑问,印刷每期份的报纸对当时刚刚满20岁的倪柝声而言是一笔很大的费用,但他从不募捐,多次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凭“信心”印刷发行。日后他回忆道,“我现在有经验,我手里越没有钱,神就越给我钱。我今日能见证说,神是供给的神。以利亚时乌鸦的供给,今天还是有的。我常经历,当我用到最后一块钱的时候,神的供给就来到。”[10] 除了编印《复兴报》外,他还赴各地传道。年,倪柝声前往上海守真堂作见证。年,倪柝声接受魏光禧的邀请,前往建瓯布道。年,他受邀请前往南京金陵大学布道,受到副校长威廉的接待。同年,他还陪同母亲前往南洋作工,建立教会等等。 倪张二人的再遇与复合 这些活动无疑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而此时,年轻的倪柝声不过还是三一学院的学生,还需应付学校的课业与考试,似乎无暇顾及情感需要。虽然年轻的倪柝声并未对婚姻显得急迫,然而倪柝声的父母早早就为他们的儿子的婚姻操心起来。随着倪氏的年龄见长,这方面的关切越发强烈。 年10月19日,当倪文修与林和平结婚时,倪文修才22岁,林和平才19岁。年,倪柝声从三一学院化学专业毕业时,年21岁,比他大3岁的姐姐倪闺臣已经为人母亲了。倪柝声作为家中的长子,其婚姻自然得到父母的重视。年11月,当时倪柝声与母亲同往南洋,林和平便迫不及待地想要为他操办婚事,虽然那时倪柝声只有21岁。林和平受从南洋回国的华侨陈良知的邀请,前往马来西亚作工约6个月之久。[11]在母亲的邀请下,倪柝声随母亲到马来西亚宣教,从新加坡到霹雳州(Perak)的锡他瓦(Sitawar),受到陈先生妹夫林提康夫妇的热情接待,并在林家居住了数周。期间,倪母觉得林家大女儿林爱倩与她儿子非常相配。在未经过倪柝声同意的情况下,向林家父母提起婚事,并且急切地要促成这事。倪柝声碍于孝道没有违抗,但是内心不安。正当他和母亲还在新加坡等候回国时,有一位学校老师设计陷害林小姐,告诉倪柝声一个故事来毁谤她的人格,他虽然不大相信,但是唯恐走错一步,在神面前祷告权衡应该怎样做。最后当他们抵达上海时,他告诉母亲神拦阻这门亲事。他一面劝母亲归还信物;一面自己写信给林家,礼貌地解释他的处境。[12]在马来西亚的事件之后,倪母似乎不敢轻易干涉孩子的婚姻,但难免会感到焦虑。 时间飞逝,转眼已到十年后的年。此时,倪文修57岁,林和平也已54岁了,对于当时社会的平均年龄而言,正步入中老年阶段。这一年,倪柝声31岁,在当时属于大龄未婚青年。倪氏作为家中的长子,其弟弟倪怀祖、两个妹妹也都已结婚,父母不能不为之心急。[13] 十年之内,张品蕙也有不少变化。由于家庭条件优渥,以及社会追求时髦的风气,加上身处经济发达的上海,张品蕙热衷于社交活动。她在上海济慈学院中表现出色,得以进入声誉显赫的燕京大学就读。她先在外文系学习英国文学,后又在生物系攻读硕士学位。[14]在校期间,张品蕙为当时燕京大学女校学生自治会交际部长。《晨报星期画报》称其为“天资敏妙,可与前任交际部长许婉君女士相伯仲。”[15] 张品蕙于燕京大学研究所读完了生物学硕士后返回上海,在上海工局部一所中学教书。、年间,她在上海听道而信仰基督,受洗成为基督徒。这个问题(信仰相异)曾经是她与倪氏婚姻之间最大的阻碍,似乎现在被消除了,而且很多人都认为她信主后有不少转变。而且已过十年,张品蕙已经32岁,仍然单身,与倪柝声一样,她也在考虑婚姻问题。回到上海后,她也去参加倪柝声在文德里的聚会,常去找倪柝声,似乎有意要嫁给倪柝声。张品蕙的二姐张品芳,看穿了妹妹的心思,便积极在其中撮合牵线。倪母也知道这些事,便常常催促婚事,但倪柝声迟迟不提婚姻的事。 倪柝声不提婚事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大原因是那时张品蕙虽然得救了,但常去跳舞场,也很爱打扮时髦。在强调属灵和“不要爱世界”的教会,属灵是婚姻中极为重要的因素,美貌、财富往往反而较为次要。而此时的张品蕙不过才得救一年,无疑在属灵生命上与倪氏极不相称。身为教会主要的负责人,倪柝声自然负有表率的责任。当教会一些同工听闻这位以属灵人著称的教会领袖即将迎娶一位燕京大学的校花,便表示反对,认为倪柝声并不适合娶张品蕙为妻。张光荣是倪柝声的同工,上海教会的长老之一,他的儿子张锡康曾说:“年下半年,倪母从福州来上海跟李渊如和我父亲商量,要我父亲出面做介绍人,使倪弟兄和张品蕙赶快完成亲事。那时,我父亲反对,认为张品蕙打扮时髦,并且出入跳舞场,不配作一个同工的妻子,他拒绝做媒人。当时也有几位女同工反对。”[18] 第二,他的婚事受到张品蕙姑母的极力反对。因为张品蕙从小失去双亲,在姑母手下养大,因此张姑母对张品蕙的婚姻比较有话语权。张品蕙的姑母有钱,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张品蕙又是名校毕业,成绩优异,尤其精通英文,而且形貌美丽,她的姑母有意要将品蕙许配给一位有前途的人,就是有名、有钱、有地位的大人物。而倪柝声不过是一位穷传道,并无多少积蓄,在上层社会眼中被看为没有出息的人,所以这桩婚事受到张姑母的极力反对。李常受说,“当时,在中国人眼中,尤其在上等社会里,认为传道人和乞丐差不多。倪师母的背景算是上等社会的家庭,因此他们不同意,尤其姑母不同意。”[19]倪柝声想到张品蕙姑母抚养的恩情,若是勉强结婚,定会招致风波。因此若非得着她的同意,他绝不肯同她的侄女结婚。[20]所以婚事就拖延了相当长的时间。 可是倪母眼看着儿子年纪已大,婚事遥遥无期,便忍耐不住,想要快快完成这一件事。[21]年10月,第四次得胜聚会在杭召开,来自全国十二省及南洋等处的信徒和同工,与会者超过四百位。特会从年10月6日晚上起,至17日止。十日之中,上下午的聚会,讲道都由倪柝声负责。[22]张品蕙也赴杭参加倪柝声主持的第四次得胜聚会。[23]长期为儿子婚事着急的倪母,一面利用这次聚会催促倪的婚事,一面去见品蕙的四叔张汝霖。由于张汝舟和张汝川相继早亡,张汝霖便成为张家的族长。在获得了张汝霖的支持后,她邀请张品蕙陪她到另一城市,去参加福音聚会,并且同室住了一个星期。回程的时候,她确信张品蕙是她儿子合适的对象。同时,倪母印发结婚请帖,定规在聚会结束的后一天,也是她的结婚纪念日(10月19日)这一天,给倪柝声举办婚礼。 倪母的这些安排,事前并没有征得倪柝声的同意。过了几天,这消息传到杭州,来赴特别聚会的弟兄姊妹,有的赞成,有的却不以为然。不少人认为最好不要把聚会和结婚的事放在一起举行。[24]倪柝声在得知母亲的安排后,似乎有意不参加婚礼。他深知若不顾张家姑母的反对,以及教会里一些信徒的意见而勉强结婚,一定会引起很大的风波。但几位年纪大的同工,认为这样作非常不好。有一位同工厉害地劝告他:“你若跑掉,不参加婚礼,对你没有问题,可是你要想到姊妹(张品蕙),在结婚的日子,新郎跑掉了,那是多么丢脸的一件事。”他又警告倪弟兄说:“若你走掉的话,我们就不与你同工了!”在同工们竭力劝告之下,倪弟兄在特会结束后,照着他母亲的意思,举行了婚礼。婚礼参加者之一的陈则信回忆道,“我记得倪弟兄事先毫无准备,他穿了一件长袍,后面还破了一个小洞。他讲道时穿的是那一件,结婚的时候还是那一件。”[25] 年10月19日,倪柝声和张品蕙在杭州东街路聚会所结婚。婚礼由长春的田品方长老[26]证婚,男方家长倪文修及女方家长张汝霖主婚,陆忠信为介绍人。[27]栾腓力做司仪,李常受做伴郎,张宜纶师母做伴娘。[28]参加观礼者计二百余人,摆宴三十桌。[29] ———转载圣经真理网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zhangzx.com/xzwh/10043.html
- 上一篇文章: 关于西藏不得不知道的冷知识
- 下一篇文章: 关于西藏不得不知道的冷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