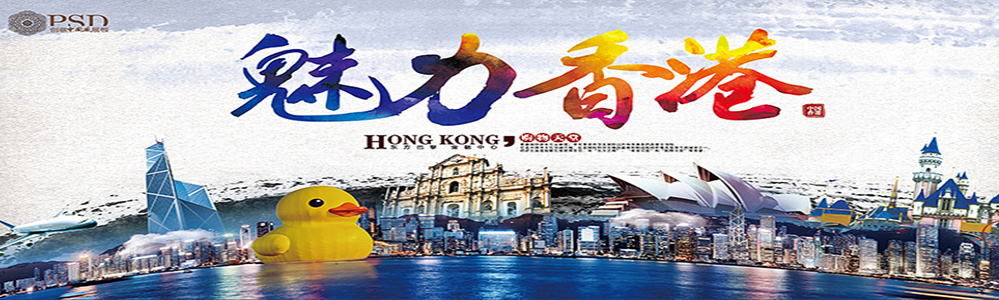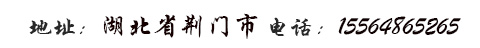乔叶风景背后名家阅读
|
作者|乔叶 来源:长江日报 一 年7月,我再一次来到敦煌。此次活动的邀请方是《今日头条》,主题是探秘敦煌“未开放区域”。敦煌我已经来过两次,按说很难再有兴致,可是地方和地方不同,新疆、内蒙古、西藏、云南和贵州这些地方我都去过不止一次,每次去也都是兴致盎然。敦煌也是如此。更何况还有“未开放区域”的诱惑呢?这个信息量丰富的词组,我喜欢。 早饭过后,八点一刻,我们在大堂集中出发。整个团队有将近三十人。第一站是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在外面的广场上等工作人员办手续的时候,我注意到了“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这几个巨大题字,落款是久仰其名的段文杰先生。随身带的《莫高窟史话》中就有不少关于他的段落。这本书是敦煌研究院编著,樊锦诗先生主编。段先生是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樊先生是第三任,刚刚卸任。我随身带的另一本书是刚刚上任的新院长赵声良先生的著作《敦煌石窟艺术简史》。说来不好意思,我曾一直把敦煌石窟等同于莫高窟,读了他的书才知道,莫高窟是敦煌石窟,敦煌石窟却不止于莫高窟,还有西千佛洞,还有榆林窟等等。 在诸如此类边走边读的过程中,我也渐渐懂得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真正意义。万卷书就是万里路,万里路就是万卷书,要想当个好读者和好行者,就不能只在路面和封面晃悠。之前的我是太欠缺了。因此诸如敦煌之行,于我而言更像是一种补课式的学习。唉,我这个老学生。 还说段文杰。他出生于年,年考入国立艺专国画系,师从潘天寿、林风眠等人。年,段文杰看到了张大千、张子云等人在重庆举办的“敦煌壁画临摹展”,就有了奔赴敦煌之意。年,他毕业后去往敦煌,在兰州时听到了敦煌艺术研究所解散的消息,非常失望。此时正好碰到了常书鸿先生——时任第一任院长,常先生正准备去重庆,为复所努力,让段先生在兰州等待。年,段先生跟着常先生来到了莫高窟,再也没有离开。 是的,再也没有离开。他和常先生都是。 二 给我们讲解的是位中年女士,姓宋,我们称她宋老师,宋老师相貌端丽,体态丰腴,颇有唐朝美人的韵味。她说这个中心有八个复制窟,都是精选出来的西魏、隋代、唐代等各时期的代表窟。 哦,是假的。不知谁感叹了一句。 不能说是假的,只能说是仿真。都是一比一按原窟严格模拟。宋老师严肃地纠正。 我暗笑,却也认同。是的,仿真和假,还是不一样的。 时间关系,只进了两个洞窟。进完了,导演说还需要补拍提问的镜头。我别的没有,就是问题多。好吧,我来。我的问题是,莫高窟壁画里最为经典的反弹琵琶图,仅仅是一种艺术想象,还是可以在生活中实现?——对第窟的观无量寿经变中的那个反弹琵琶图,我印象最为深刻,可以说是日日相见。二十多年前,《读者》杂志曾赠给我一个金光闪闪的小牌牌,刻的就是这个反弹琵琶。 宋老师说,她的个人观点,是倾向于可以在生活中实现的。原因么,真正的艺术不是空想,必定来源于生活。另外就是,有不少人都做过实验,果然实现了。只是反弹那一下,持续时间很短。总之,就是象征性的,是仪式感很强的一个动作。不过,那一瞬间,就是全场的高潮。 是啊,高潮总是短暂的。漫长的高潮,谁也受不了。而且,漫长的高潮,还能叫作高潮吗? 接下来就是进非仿真的莫高窟——这真是有点儿绕啊。去往莫高窟的路两侧,绿草茵茵,鲜花遍地,虞美人、万寿菊、八瓣梅……环顾四周干旱焦渴、寸草不生的戈壁和山峦,觉得眼前这景致,有些魔幻。 不一会儿,就看到了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九层楼。这九层楼是印在莫高窟门票上的,如同洛阳龙门石窟的门票印的是奉先殿的卢舍那一样,足可见其重要性。九层楼是俗称,官称是第96窟,里面是莫高窟第一大佛像,高达35.5米。因此还有一个俗称是“北大像”。九层楼正前方是刻有“莫高窟”三个大字的牌坊,这是所有游客都会留影的地方,我前两次来,都在这里拍了照。 游客的队伍很长,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宋老师说,暑假总是这样人满为患,对景区而言压力挺大。人多,对洞窟的伤害就大。五个人和五十个人,在空间那么有限的洞窟里,温度能一样吗?湿度能一样吗? 莫高窟的旺季是什么时候?我问。 5月份到10月份。其实,其他淡季来看,也相当不错。 淡季你们也上班吗?问过后就觉得自己的问题好白痴。 是啊,上班。她很平静。说尤其是冬天,尤其是冬天的雪后,没有多少游客,那个时候的莫高窟,特别特别美。 雪后的莫高窟,让我充满了向往。我相信,一定是特别特别美。 三 获得了特权的我们没有排队。但被通知只能进两个窟:窟和窟,且每窟只能进六个人,含一个摄影。于是工作人员把我们分成了两组,我在第一组。 屏声静气地,我们几个鱼贯而入,进了窟。窟里光线昏暗,适应了片刻我才看到,里面有几位技师在静静工作,整个窟内鸦雀无声,和外面的喧闹仿佛是两个世界。站在窟里,我们的声音都不由自主地低了下来,怕打扰了他们,以及墙上的壁画们。 我对此窟做过一些功课。这是中唐的代表窟之一,开凿于公元年,是吐蕃统治时期阴嘉政阴嘉义兄弟所建,亦称阴家窟。——是的,敦煌也曾长期失守,被吐蕃统治。在吐蕃统治期间,身为世家豪族的阴家成为了吐蕃的主要目标,在恩威并施的拉拢之下,阴家众多子弟都出仕吐蕃,日子虽然太平富贵,甚至可谓一门荣宠,却也有难言深痛。阴嘉政晚年常常忧郁不已,认为自家忠义有亏,于是和弟弟阴嘉义开窟求功德,第窟由此得建。此窟东壁门上有阴嘉政之父阴伯伦及其母索氏的供养像,壁画上的阴伯伦头戴璞头、靴袍革带;索氏头梳抛家髻、长裙帔帛,夫妻两人都是汉家装束。此时他们都已经亡故,所以可着汉装。那些在世的阴家人,还都必须穿吐蕃装。服饰的意义不止于服饰本身,各种滋味,一言难尽。 负责接待我们的修复技师是杨韬老师。他穿着蓝色工装,小麦色皮肤,身材健壮,朴实敦厚,一看就是典型的西北汉子,说话也是浓浓的西北口音。他腿脚不太好,似乎是带着伤病。我们不提问的时候,他也不多话,就那么安静地等待着。讲到修复的细节,他的话才多了起来,说他在摸索尝试更好的方法。他把我们引到一面墙前,用手电筒照着一小块地方,那地方也就是大拇指指甲盖大小。他说,修复这么小的地方就得花大半天。 技师里有一位女士,相貌娟秀,我便蹲到她身边,想和她聊几句,可她专注的样子却让我不大好意思打扰了,只是打了个招呼。她微微地笑了笑,那一瞬间,她的眼神,真是清澈。 对于文物修复,我仅有的可怜知识都是从《我在故宫修文物》一书中读来,一读方知深似海:雕塑、书画、壁画、器具……不不不,准确地说,像我这种水平的,连海也不知,大概也就是拿着望远镜望见了海的蓝吧。 后来我看同行者发的头条,说:“……虽然曾经来过十几次,看过许多窟,也在日常聊天中,眉飞色舞地为自己看过多少窟而骄傲自吹,但每一次,当脚踩入,依旧是那种难以言状的,不敢呼吸的震撼。我想,我所能想的,便是‘一花一世界,一窟一宇宙’……脚下的雕花地砖,那是西夏的遗物。据说,美国专家曾给这些西夏方砖估价过,每块8万美元,现在为了谨防游客踩踏,已用木板覆盖上。” 地砖这么贵,我有些意外。有些后悔在窟里时不曾留意。——是因为它贵才想留意的吧?是因为贵而觉得应该好,而不是因为好而觉得应该贵吧?这就是如我这般俗人的思维吧。 上到二层,就看到了完整的窟顶,为覆斗形,专业称呼是“华盖式藻井”,周围布满千佛,飞天旋绕。看西壁,有三身塑像,中间造型奇特,资料中说这是双头佛像。窟内壁画的内容则全都是经变:《文殊变》《普贤变》《天请问经变》《法华经变》《观无量寿经变》……所谓经变,就是佛经内容或佛传故事。经变题材在吐蕃占领时期层出不穷、多姿多彩、多种多样,有效地拓展了莫高窟的艺术格局。“家国不幸诗家幸”,对于壁画而言,似乎也是如此。 出了洞窟,阳光灿烂。我不由得眯了眯眼睛。仿佛重新来到了这个世界。 这是张大千留下的编号,还有点儿痕迹。杨韬老师指着窟门口的南墙上方说。 国内画家里,张大千是第二批去敦煌临摹的。第一个到敦煌的画家叫李丁陇,祖籍甘肃陇西,生于河南新蔡,是刘海粟的学生。年,他和另一位画家到达敦煌,在这里待了八个月,第二年在西安举办了“敦煌石窟艺术展”;年,他又到成都和重庆办展览,张大千看展后深受影响,也去了敦煌。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带领弟子们临摹了壁画两百多幅,大受滋养。他们所排的敦煌石窟编号被学术界采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四 两组聚齐之后去吃工作餐。饭后原地休息时,有人号召去拜祭敦煌前辈学者们的公墓。问我去不去?当然要去。于是就跟着众人出了门。乍一回到烈日下,头微微有些晕眩。就把脚步放慢了一些,稳住了神。众人看着路边的花草和滋滋作响的喷灌机,感叹着说这成本太高了。 水这么珍贵,没必要一定用在这里。有人说。 就是。假花假草也可以的,反正来这里也不是为了看这些个。有人附和。 那边的窟是假的,这边的花草是假的……有人犹疑。 游客是真的。有这一样真的就行了。有人打趣。 说笑着,就过了大桥。桥下有河,这河里……有水吗?几乎没有。查资料,这河,叫宕泉,也可以叫荡泉,还有一名为大泉,因其源头在莫高窟东南四十里鸣沙山东麓的大泉。 ——源头居然在鸣沙山东麓。这是一条什么样的河啊。没有水也值得敬佩。不过,仔细看,阳光下碎钻一般闪亮的波流,还是有一些的。毗邻着浩浩荡荡的沙漠戈壁,这一脉细流貌似那么脆弱,可是居然也没有断掉,又可见柔韧至极。 先是看见了一些塔,也不知道塔下都是什么人。想来也许是大德高僧吧。再往上走一走,就看见了那些墓碑。我知道,这就是他们了。 一块碑一块碑地走过去,在每一块碑前鞠躬,祭洒一些纯净水。无花无酒的我们,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敬意。这一刻,我觉得,用纯净水向他们祭拜,也许是更适合的。 碑群的最高处,安息的是常书鸿和段文杰。 常书鸿,年公费留学法国,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里昂国立美术学校,之后通过了里昂赴巴黎的公费奖学金考试,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深造,作品在法国国家沙龙展中多次获奖,后来在巴黎娶妻生子,日子过得富足安逸。直到他在巴黎街头看到了柏希和当年在敦煌拍摄的敦煌壁画图集,大为震惊。年,他毅然回国,时任国立艺专教授,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战乱开始。七年的颠沛流离之后,年,他才来到魂牵梦绕的敦煌。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他成为了首任院长。除了临摹壁画,这位院长做的还有什么事儿呢?给石窟安门,在窟外修墙,晚上还要拿着棍棒巡夜,以防盗贼……就是在这里,他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因先天不足而夭折,孩子的名字叫沙妮,沙洲之妮——敦煌,又称沙洲。 告别的时候,在猎猎风中,我们又一起向他们的墓碑鞠躬。身后就是莫高窟,就是无数游人。我一厢情愿地想,我们是在替这些游人向他们致敬。 回程的时候,我特意往上走了走,直到把他们的墓碑全部纳入镜头。他们的墓碑正对着的,就是高高的九层楼。这一刻,我仿佛拥有了他们的眼睛,替他们在看着九层楼,看着莫高窟。 热泪盈眶。 仍是一路闲话。他们说到了樊锦诗。樊锦诗,这位老太太,被称为“敦煌的女儿”,见过她的人都说她“气势如虹”。我见过她的照片,很瘦,戴着眼镜,花白的头发很浓密,精神矍铄,灿烂的笑容里有挡不住的强硬。是的,有些人就是如此,他们的笑容都是有骨头的。 年,樊锦诗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前夕,她和同学到莫高窟实习,毕业之后,她义无反顾地重返这里,开始了自己的敦煌人生。她的丈夫是大学同学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当老师,后来她让丈夫把大孩子带到了武汉,第二个孩子则让上海的姐姐抚养。无论多么艰难,她对敦煌,对莫高窟,都没有动摇。上世纪70年代后期敦煌研究院重入正轨后,她和马世长、关友惠等专家们的一批论文发表,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年,莫高窟成为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对于片面强调要用文物来开发经济效益的观点,她深感忧虑,多方奔走,使得《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出台,莫高窟终于有了护身法。此外,与国际科研机构合作,对壁画和彩塑的病害进行深入研究,对窟外的风沙进行预防性治理,运用先进科技记录和保护石窟的精美艺术……都是她孜孜以求所做的事。 年,段文杰卸任,樊锦诗成为第三任院长,此时的她,正好六十岁。如果是别的什么院长,六十岁肯定有些老了。但是这是敦煌研究院啊,我觉得六十岁特别合适,简直是再合适不过的年龄了。 五 在莫高学堂学画壁画是最为轻快的。进到学堂里,在蒲团上坐下,蓦然看到面前摆着的小壁画正是第窟的观无量寿经变中的那个反弹琵琶图。线条其实已经画好了,我们要做的,只是涂色。这画不是在一般的纸上,而是在一小块模拟的墙坯子上,厚度约有一寸。壁画壁画,这就是壁了。 泡开了小毛笔,打开了国画颜料,开始下手涂。相比于画线条,涂色似乎容易一些,但一下手就知道不容易。想要翻看原图,老师不允许,说会限制想象力。 孩子们来这里,我们都是这么要求的。你们也一样。老师说。 这是把我们当孩子了?也好。尽管我们肯定不如孩子们,但能够享受这份待遇也不错。可是,想象力啊,你在哪里呢?早就被紫陌红尘消磨殆尽了吧。脑子里能回忆的,只有看了无数遍的原图。恍惚记得有青、黄、绿……管他呢,凭着感觉走吧。 真正开始之后,就不再犹疑和焦虑。心也越发静了下来。一笔,一笔,着了魔似的,不再想其他。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画似乎是静的,人似乎也是静的,但是人去画的时候,哪怕只是涂色,静就变成了动。而这动,又是静静的动。 老师巡视过来,表扬我说体现出了一些唐代壁画的风格。我心更定。是啊,我爱唐代。不仅仅因为我是个胖子。每个朝代都有每个朝代的气质,唐代的气质,雄浑、艳丽、阔大、强悍……太迷人了。 沉浸在其中,不知不觉,就进入了这个小小的世界。听不见别人的说话,也忘了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zhangzx.com/xzxw/14080.html
- 上一篇文章: 二本算不算差,上二本学校有用吗微雨润苗
- 下一篇文章: 云瞰中国丨风景旖旎壮美,风情醉人心弦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