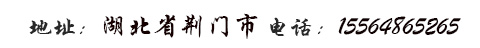经历马明月我的同学李福安,西藏漂泊
|
文/马明月 (马明月,年毕业于陕师大中文系。现在新疆,职业警察。) 那个淫雨绵绵的秋天,我的心底充满了阳光,揣着一纸入学通知书,带着一堆行李和一团混沌的梦想,来到了大学校园。 报到的时候,见到一个穿花衬衣、喇叭裤,留着长发,蓄着小胡子,嘴上叨着烟,脸上透着一股凶狠的家伙也在附近溜达。心想,社会上的流氓怎么也混到大学校园来了? 第一次班会,辅导员点名让大家相互认识,又见到那个家伙了,一脸阴郁,不苟言笑。靠,原来是我一个班同学!还有一个很草根、很市井的名字:李富安,一听就没什么大志向,小富即安嘛!我仔细端详了他:小长脸、高鼻梁、细迷眼。因为瘦,脸上颧骨突出,有几道深深的抬头纹,一开口一腔河南话,显得凶巴巴的。 他是西安人,住在城北关外二马路一带。后来和富安成为朋友后常去他家,搞清楚那是个什么地方。那里靠近火车站,被称为“道北”,大部分居民都是当年从河南来的逃荒者,沿铁路线聚居,形成社区,属于社会底层。当时有一句顺口溜“出了北门上北坡,贼娃子野鸡一窝窝”就是说这一带。在西安城,只要讲河南话,说是道北的,都没人敢惹,他们争勇斗狠,强捍霸道,在西安火车站一带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人的“碰瓷”、讹人。富安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曾说,如果不是考上大学,他可能就是走向社会的一个流氓。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一部纪实电视剧“枪响了,出事了”的《12·1枪杀大案》,里面的那个外号叫“小黑”的黑道老大魏振海,就是道北人。富安还认识这人,提起他,富安一脸的不屑:我们在街上混的时候,他还是个屁孩! 李富安长了一副好身板,高挑个,细长腿。我们那个年代出生的人,小时候卡了食,发育不良,普遍腿都长不直,有的甚至是罗圈腿。富安那两条平直的双腿,让我们煞是羡慕。富安没有亏待他这付好身材,很注意穿着形象,总是穿着得体。白衬衣永远是一尘不染,长长的喇叭裤裤缝永远是棱角分明,皮鞋总是擦得明亮,一付绅士派头。有时候,挺刮的衣服不是穿,而是披在肩上,一只手扯着衣襟,很拉风。除了穿着用心,其他干什么都是随心所欲。在宿舍很少叠过被子,上课不记笔记,有时几天见不着面,和辅导员、学生干部对抗,经常醉得不省人事。总之,在组织上和学生会干部看来,他不是什么正经人。 入校头一年,富安爱和高年级同学厮混。那些家伙都是老江湖了,有的下过乡,有的当过兵,有的做过工,思想敏锐,阅历丰富,处世有分寸,富安竟然能混进他们的圈子,他比我们成熟。学校组织的一些文学、文艺社团啊、学生会活动啊等等,凡是组织上搞的活动,他都嗤之以鼻,不仅不参加,还嘲笑挖苦我们,好像参加这些活动都是做见不得人的事。也不见他用功学习,尽读些与考试无关的闲书,晚自习室很少见他,直到毕业,他的英语成绩都没有过关。但是一旦认真讨论起文学美学问题时则很有见地。对我们花花草草的文学习作他都看不上眼,从来没有肯定过。这让我们很恼火,一个这么不靠谱的人居然眼光这么高。 他尤喜欢苏联当代文学,《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方尖碑》和阿赫玛托娃的诗歌都是他极力向我推荐的。我翻出了当年学校文学社编的一份文学刊物,里面收了他的一首诗《里程碑》。现在看来,那份刊物里的东西都充满了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学生腔,而他这首诗放在现在来看也是成熟的。其中有一节是这样写的:“我第一次红脸/是看见大家都在脸红/我也许不甘落后/就作了这样的补充”。他的笔名是“扬尘”,问他为何取这名儿?他说,撒一把土,我就是要给这世界找点小麻烦。 他既不会唱歌又不会跳舞,但又爱往人多的地方凑热闹。只要年级和系里的舞会,他都和我们一起去参加。常常一直坐在那里聊天,抽烟,偶尔打个口哨、喝彩起哄一下。那年,中国女排首次获得世界冠军,学生们不听校方劝阻冲出校门庆祝游行,像过狂欢节。这家伙混在人群里疯狂闹腾,喊哑了自己的嗓子,敲坏了系里的大鼓,差一点把自己的衣服都烧了。我们都是同龄人,但富安似乎更成熟,社会经验丰富。出去游玩,他是大家的主心骨,有他在身边就不怕社会上的混混流氓。一付凶相加上一口狠硬的河南话,没有人敢挑衅,应了多少年后流行的那句话:我是流氓我怕谁? 不知为什么,他总是内心充满痛苦,老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样子。在街上看到一个乞丐他都要感慨半天:怎么就没人管呢?仿佛那些孱弱的灵魂里都有他的影子。一次在学校同学小聚时,他喝的红头涨脸,语重心长向大家说了句貌似很有哲理的话:“人生就是为痛苦而生的,做好承受痛苦的准备”。当时大家都很不以为然,大学生天之娇子,前景美好,阳光灿烂,有什么可痛苦的?认为他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其实那是他自由飞扬的灵魂在现实中处处碰壁的结果。哪个鬼佬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富安可能最先体验到了。 他喜欢上了学校某系的一个美丽素雅的姑娘,那可是学校的校花啊。这家伙不知深浅地爱的死去活来,不惜放下大男人的身架,写了一篇又一篇诸如“我的爱人是温柔婉雅的/它是暮辉中闪耀的水光/隐入玫瑰色的空气中”等等肉麻的诗歌,托人送去,每日痴痴地隔着操场遥望对面楼群女孩宿舍。我们都劝他,你都长成这样了,怎么还有这份妄想?开始女孩很害怕,以为是流氓骚扰,还报告了校保卫部。富安用他诚挚的心和时间证明了他的纯真感情和他是一个好人。后来,如我们所料,根本不会有结果,但二人成了朋友。那年秋天,外语系楼前的枫叶红透了的时候,他摘下一片红叶对我说:不谈一次恋爱怎么能成熟起来?遇到心仪的女孩怎能放过放飞感情的机会? 常在社会上游走,富安身上积了一些江湖习气,为人仗义,吃软不怕硬,遇到看不惯和不讲理的事情便破口大骂,甚至动手。一次中午在食堂排队打饭的时候,一个学生蛮横地加在队伍前面,没有人敢吭声。富安从后面过去,揪住那人的领子从队伍中拖了出来,对方也是个火爆性子,没过两句嘴,两人轰轰烈烈五马长枪地挥起了硬拳。打完后,富安擦着嘴角上的血,钦佩地说:这家伙有种,敢和我动手!对方不光是有种,还有非凡的背景。原来,那学生是从四川大凉山来的彝族学生,据说是其先人是个什么土司贵族,现在家里也在政协里当差。这下富安摊上大事了。那彝族学生告到了学校,要求开除李富安,否则回老家叫人来剁了这个胆敢冒犯贵族少爷的刺儿头。就在学校要顾全大局,息事宁人准备处分李富安的时候,这个彝族学生又到校党委去求情,不要给这小子处分了。原来,不打不相识,那边学校正紧锣密鼓准备开出罚单的时候,这边二人惺惺相惜臭味相投已多次会晤,不但和好,还成了朋友。校方火了,学校是你家的庄园?你说啥就啥了?李富安必须处分,严重警告! 毕业分手时,班里只有富安最悲伤。在人去楼空的教室,我看他伏在桌子上像个孩子般痛哭长涕,脆弱得像失去了生命的支点。是不舍给自己带来温暖和快乐的同学?还是留恋阳光明媚的大学生活?后来他不止一次说过:大学四年像梦境一样,是这一生中最美好瑰丽的岁月。 把同学一一送上西去东往的火车后,富安去了西藏,一呆就是十年。他认为西藏十年重新铸造了他的灵魂,使他自由随性的天性充分得到了释放,也只有在那里他才能无拘无束,天马行空。庸常的生活常常被他过成传奇故事。有一年夏天,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年轻人找到我家,说是从西藏拉萨来的,李富安让他来找我。他告诉我,他是李富安的朋友,是从川大毕业援藏的。晚上吃饭时他给我聊起富安的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有不少人去西藏探险旅游,那时吃住行还很不方便。富安无所牵挂,仗义大方,他在西藏拉萨的家成了旅行者的驿站,成了交结天下豪杰的聚义厅。这些行者回去后口口相传:到了拉萨去找李富安。找到门上,只要报上是谁谁让我来的,就住下了。有天他下班回家,竟然有几个陌生人在他的宿舍里开伙做饭。富安诧异地问:“你们是谁”? 回答:“我们是李富安的朋友”。 “我就是李富安,我不认识你们啊”? “噢,我们是从北京来的,是xx让我们来找你的”。 那就啥也别说了。煮肉沽酒,一间陋室成了华丽的宴会厅,一群江湖游子在风寒的高原找到了温暖。 在西藏混迹了十年,在那里他和一名比他大几岁的四川女人结婚成家,有了自己的儿子。下山前,他头发稀疏了,脸灼黑了,抬头纹更深了,嘶哑的喉咙,再也唱不出清冽的歌了。带着一身疲惫和一车野牦牛头头骨,回到了西安。据说带回的那些野牦牛头放在地下室,没有及时处理都臭了,后全部丢弃。在高原工作拿的是高工资高补贴,那时西藏也没有多少消费的地方。但下山时,他没存下一分钱,千金散尽,裸身而归,连媳妇都没有带回来,他和老婆分手了。 回到西安,他的精神和身体调整了很长一段时间。流逝的岁月和纷繁变化的社会没有改变他,他还像过去一样,随性,倔强,不妥协,没有耐心和这个世界对话,所作所为完全和社会脱节。他被分配到西安市某政府部门,过着规矩呆板的机关生活。因为很强的业务能力要提拔他了,却发现他还不是党员。有人动员他入党,他说:都坚持那么长时间了,我不能晚节不保,贵党条件高,我达不到。竟然给组织出难题。后来听说加入了一个民主党派,算是有了个政治身份和归宿。我们都担心:同学、朋友可以理解你,包容你,在单位,在社会,你这样的生活状态,还有人允许你这么任性吗? 一次我到西安出差,他来到我住的宾馆,与我畅谈。已经很晚了,我说你回吧,明天还要上班。他说,我就住这了,明天不去上班了。躺在床上,他手中的烟一根接一根不离手,房间里云腾雾罩,还不时地朝地上一口一口地吐痰。我实在忍不住了:“能不能少抽点,能不能不在地上吐痰”?他小眼一瞪:“不能!咋了?”就这么聊着、扯着,一直到后半夜。渐渐听得他鼾声大起,见他已经睡熟,我起来关了电视。突然他就醒了:“谁关电视了?把电视再打开。”听着电视他又睡着了,我却头脑昏昏瞪着眼睛等天亮。 前年夏天,他随着一个旅行团来新疆旅游,到了乌鲁木齐就离团了。去他的山水风景,去他的旅游观光,我要和弟兄一起畅叙畅饮,我要和同学们共度好时光!同城几个同学,分别放下手中的工作,整天和他厮混在一起。整整一个星期,我们都快受不了了,这家伙还兴致盎然,看样子还想再住一个月。听南国的同学说,这家伙到深圳出差,和同学啸聚畅饮,酒酣耳热际,竟把第二天的火车票掏出来撕了,说,明天不走了,我们再喝一个晚上! 岁月荏苒,富安那颗躁动不安的心也该平静下来了吧?残酷而丰厚的生活带给他伤痛,也平添了他的力量和智慧。儿子长大了,聪明可人,从西安交大毕业。富安卖了家里的一套房子,凑出钱送孩子到美国去念书。他又重新成家了,他老婆我见过几次,贤惠开朗,能容忍他那么多毛病的女人,真的是个好女人。富安的老母亲还很硬朗,一个人住在老屋。他说要将前妻从成都接来,让她和母亲一起生活。前妻和他离异后再未成家,一直和儿子相依为命。儿子远去美国,她孤身一人在成都。“我什么都有了,她什么都没有了,我要把她接过来,养起来”,富安这么说。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许巍这首辽远深情的《蓝莲花》,像是唱给自己的乡党富安的。我又静心谛听一遍,往事如烟,若隐若现。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zhangzx.com/xzys/6981.html
- 上一篇文章: 下午想旅行,晚上到西藏你敢不敢跟我一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