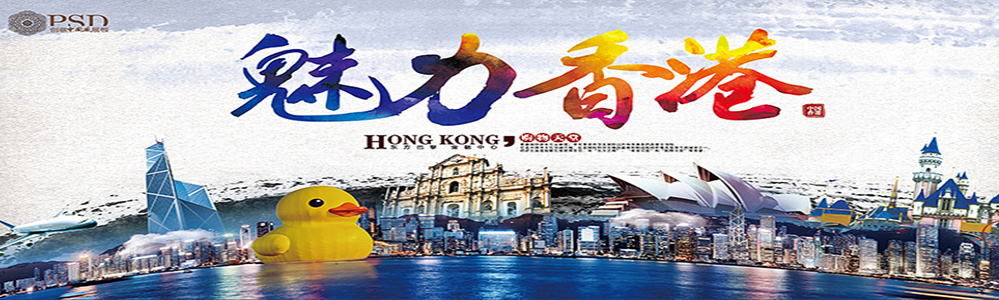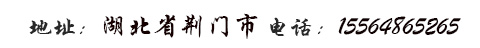读书,农二代逆袭的最后一根稻草陕西法制
|
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大学是他们走出农村,去看外面世界最好的机会,也是改变命运的开始。真正的寒门不是贫穷,而是屈从于贫穷之下的绝望,你自己都放弃了追求更好的人生,怎么还会有逆袭的可能? (摘自搜狐网《致所有出身贫寒的学子:农村孩子逆袭是不是真的没有可能了?》) 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出生豪门的,我们都要靠自己,所以你要相信,命运给你一个比别人低的起点,是想告诉你,让你用你的一生去奋斗出一个绝地反击的故事。 (摘自北大刘媛媛演讲) 对于80年代的农二代来说,要想改变命运,除了读书,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路子可走。 老K的祖辈都生活在农村,在50年代划分农村成份的时候,老K的爷爷成份不好。后来听奶奶说,当时家里面省吃俭用节约出钱来,置办了少许田地,略比好吃懒做的懒汉稍微好一点,奶奶去世后,具体规模就无从查证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相比如今,动不动就是几千上万亩圈地,搞农业项目,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 由于成份不好,生存是极为艰难的。那个时候成份很重要,以贫穷为光荣,越贫穷底气越足,越有优越感,越感觉自己是又红又专。据奶奶回忆,爷爷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由于无法忍受无日无夜的打骂批斗,只得申请去劳教,最后死在劳教队,至今连尸首也不知道具体在何处。 在父亲的印象中,他大概读了两三年书,不是自己不想读书,而是根本读不下去。像父亲那一辈人,出生在50年代初期,正是国家困难时期,首要任务是填饱肚子。但据父亲回忆,小时候也基本都是饿肚子,吃野菜,吃树皮,吃黄泥巴。幺爸吃泥巴后,拉不出来,还是奶奶用剪刀到屁眼里面去掏,才掏出来的。他们年龄大小差不多的,也有一些人被活活的饿死了。当时是怎么活出来的,连自己都不知道。 听父亲说,他每次去读书的路上,都会被同一个院子里面的一些同龄小孩拦住,不让他去学校。在学校里面,也经常受欺负,最后没有办法,想读书而读不成。 残酷的现实,导致了父亲的一生,也就勉强能认识1-10的数字,勉强能歪歪倒倒地书写自己的名字,算得上是地地道道的文盲。这有什么办法呢,农村青壮年,该读书的年龄被荒废了,知识文化比较少,能写自己名字的,都算不错了,唯一能开发的,也只有自己的那一身骨架+血肉。 老K自然就成为了文盲的儿子。但这也怪不得谁,这或许就是命运的安排。 父亲也没有多的语言,也不会说那么多大道理,就用他自己的理解,朴素的语言和实际行动来言传身教。父亲给人记忆中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自己要争气,争取把农民壳壳脱了”。言下之意,就是争取以后不要继续在农村、当农民。 父亲是一名石匠,这是他早期唯一能养家糊口的手艺。而这个手艺,在90年代中期以前(或许更早),还有一定市场,那个时候石材是修房子的主要辅料,但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烧砖窑的兴起,方块砖取代了石材的地位,父亲也就渐渐失业了。 老K出生的时候,由于是二胎,听父母说还被罚了多块钱的款。当时父亲在外面打工,那时候他的身体比较硬朗,1米7左右的个头,就随附近的农民一道,到偏远山区抬电杆去了。那多块钱的罚款,也是牵猪收粮、东拼西凑,加上父亲的苦力钱,才算凑齐。 由于线路上是重活,随着父亲年岁的增长,后面年份人家也不要了。父亲就只得继续靠着田土过活。 为了供姐姐和老K读书,父亲和母亲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得靠布满老茧的双手和磨破血肉的双肩,起早贪黑,在土地上挖刨,想法设法来增加收入来源。大致有这么些途径。 其一,多种田土,卖粮食。那时候,打工潮已经开始,村里面不少人开始外出打工挣钱,田土自己不种就荒了。父母就把同村荒了的田土,尽最大努力多种一些,印象中最多的时候是3户人家的田土。一年四季、寒来暑往,基本都在田土里面挖刨。到了秋季,收了水稻,先是给公社交粮,再留足口粮,余下的全部卖掉。 其二,喂养母猪,卖猪仔。那个时候村里面家家户户都要喂猪,一般来说是2-3头,喂养一年,到寒冬腊月,猪儿肥了,就杀1头,人口多的可能就杀两头,余下的就卖掉。卖猪的钱,基本上是整个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也是最大头的一笔收入,可以用来为来年买猪仔、买化肥和供孩子读书等大额开支。然而,这也是一个技术活,好的光景,一头母猪一胎可以生上10头小猪,少的也有3-5头,但稍不注意,也可能全部打水漂,一窝猪还没长到可以卖的体格,就生病死掉了。印象中,家里面养了3年的母猪,最多的时候是两个圈两头母猪,刚开始的两年还不错,但到了后来就养得不顺了,猪仔存活率不高,不但赚不了钱,连本都得赔进去,也只得作罢。 家里面猪的一日三餐,大多是被母亲承包的,到了农忙时节,白天要出去干活,往往是头天晚上,就把第二天的猪食准备好,熬上一大锅包谷面混合猪草的猪食。 由于母亲白天干活已经精疲力尽,十分疲惫,往往是一边打瞌睡,一边砍猪草。在我的印象中,不止一次,母亲实在太困了,左手握着红苕(薯)藤(一种猪草),并将藤压在木板上,右手拿起刀往下砍,把红苕藤砍成2-3厘米的短截,煮烂后便于猪吞下去消化。就在手起刀落的时候,由于双眼打架,右手瞬间砍下去,直直地砍在左手上,鲜血直流。“哎哟”,母亲顶多喊叫一声,从没见母亲因为手被砍而哭泣,有时候实在痛得不行,眼泪也难免忍不住要往下掉。 看到母亲握着被砍还在流血的手,我都十分害怕与心疼,感觉那把刀仿佛就是砍在自己的手上。直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母亲的左手上,还有若干道伤痕,大多是被自己砍伤的。这些都成了岁月的见证! 其三,种芋头,到场镇上去卖。为了便于平时管理,一般选择了在离房屋最近的一块田里面种芋头,收完了稻子就开始种植。最考验人的,是挖和洗。一般是冬天最冷的时候开始挖,必须忍受刺骨的寒冷,父母的手,一到冬天,基本都要张多条冰口,稍一用力,就会有血渗出来。芋头要买,必须得在赶场天到乡镇场镇上去,得头一天下午就开始挖和洗,洗干净之后就开始剪母芋头上的毛须,然后装框或者装袋。这项准备工作做完,基本上就到了晚上九十点钟。由于隔集镇比较远,为了赶在开市之前到达,同时还得占一个叫卖的摊位,父母往往是凌晨3-4点就得起床,也来不及吃早饭,就得出发。父亲用扁担挑一挑,母亲用背篓背一篓,一前一后,打着手电筒。最糟糕的是,遇到下雨天,时间又不能错过,也只得头顶戴着草帽或打着雨伞,身上披一块一米大小宽窄的白色薄膜,把两个肩膀和背部遮挡住,尽量不让雨水直接淋到身上,这也就算是父母发明的“简式雨衣”了。尽管采取了保护措施,但到了场镇,全身基本上还是被雨水淋个半湿,皮肤上冒着汗,头顶上冒着烟,身子上流着水。早些年,从家到场镇,还没有通公路,每逢3、6、9日赶集,赶集都是走路去,大约需要50分钟。后来通车了,父母也舍不得花1块钱(后来涨到1.5-2块),仍然是走路去。肩挑背扛几十上百斤的芋头,至少得1个半小时,到了集镇天还没有亮。运气好的时候,中午十一二点基本可以买完,有时候卖的农户多了,也免不了要背些回去。 为了供老K上学读书,尽管父亲的年龄已经偏大了,但还是迫不得已要做重体力活,争取尽可能改善家里面的经济状况,纵然如此,直到老K大学毕业,家里面还是欠了一万多块钱的外债。每想到这些,老K都为自己无法及时尽孝,减少父母的负担而深感自责,十分愧疚。 如今回想起来,都不知道那些年,父母是怎么熬过来的。但后来,据他们说,那些岁月也算不得什么,至少还有吃的,比起5-60年代他们还是小孩的时候,好得太多了。父亲说,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粮食吃,就吃树皮、吃野菜、吃黄泥巴。母亲告诉我,她到5-6岁的时候,都还不会走路,主要是营养不良,她们同村的一个同龄人,还被活活的饿死了...现在,土地分配到各家各户,只要不赖,至少嘴巴还能糊住,肚子不会挨饿。母亲说,她们那辈人,都饿怕了,眼前这点苦头,算不得什么! 或许是受父母辛苦劳作的感染,或许是受父母言传身教的影响,或许是穷人家的孩子醒事早早当家。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老K稚嫩的心中,逐渐升腾起了改变处境的愿望,开始有了强烈的学习热情。 印象中,这个阶段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的,老K11岁左右。从村小到乡小,六年级开始,老K当上了副班长,仅次于学习委员、班长之后。那个时候的班干部,完全是班主任按照学习成绩来安排的。到了初中以后,继续延续班副一职,班长由一个身材高挑的同学担任。记忆中,初中开始,白天耍得比较疯狂,由于没有钱买足球,就用矿泉水瓶子当足球踢,同学们踢得那是噼里啪啦,尘土飞扬,雨天更是全身泥泞;后来同学们筹钱买了足球,下午放学后,更是不到天黑不回家。夏天,更是胆大妄为,中午拿着集中蒸好的饭菜,就和同学们集体到附近的池塘里面去洗澡,一泡就是一个中午。那个时候,都是自己早上从家里面用铁瓷盅具,条件好的同学用的是不锈钢饭盒,写上自己的名字或者打好标记,将土豆、红薯、芋头、胡豆、玉米等,晒上一些盐,搅拌均匀,作为垫底料,然后将米粒倒在上面进行覆盖,也有的家庭条件好的同学在米里面埋上一些肉,到学校后统一放在箩筐里面,拿到食堂里面去蒸熟,临近中午下课的时候,每个班会派4名左右同学到食堂里面去把蒸好的饭盒抬到教室。下课后就自己端自己的饭盒享受大餐。 尽管老K玩耍得疯狂,但学习成绩并没有受影响,主要得益于把早上的时间用得好,养成了早晨看书的习惯。每天早上4点左右,也就是母亲起床做早饭的时候,老K就翻身起床,开始看书,背诵课文,尤其是语文、政治、历史、英语等课程。 记得有一次,印象特别深,母亲在灶屋拉着风箱烧火做饭,老K和往常一样,也翻身起来,拿着书看得正有劲。突然,听到房屋的背后,仿佛有婴儿在哭泣,开始还以为是听错了,没在意,后来声音越来越大,越哭越悲惨凄凉,自己倒吸了一口冷气。什么情况?这附近没有谁家生小孩呀,怎么会有婴儿哭声呢?一边寻思着,一边听着嚎叫,越发感觉吓人。小时候,经常听大人说一些关于妖魔鬼怪之类的事,心想莫非真的有鬼。吓得不行。于是,老K赶紧关灯,拉上铺盖,迅速地把头蒙了起来。即使这样,还是有婴儿哭,只好越发把铺盖裹得更紧,由于担心真的是鬼,也不敢作声向母亲呼喊,只得在铺盖里面熬到天亮。 待到天亮以后,才试探性地问母亲,早上是不是听到婴儿哭泣了。母亲才说,那不是什么鬼怪,是猫在叫春。这才放下心来。在以后的岁月里,也不时听到猫儿叫春,老K再也不怕了,权当是猫儿在醒瞌睡。 天道酬勤,功夫不负有心人。整个初中阶段,老K的学习成绩都排在学校前列,在初二的一个学期,更是以全镇第二名的成绩,在整个镇上形成一定影响,在附近几个村更成为父母教育小孩的榜样。 初中毕业之际,又以较好的成绩考上了全县和全市的重点高中,成为全校仅有的3名同学之一,到市重点高中就读。印象中,全校3个初三班,学生人数超过人,分数线上全县两所重点高中(县一中、县中学)的大约20人左右。其余的要么读镇上或隔壁镇的高中,要么开始承担生活之重,开启打工的活计。 市里面的高中,被坊间称作是干部子弟学校,都说是当官的或者老板的子女就读的学校。当时的老K,对这些还没有特别强的概念。他们那一批次,有点像高考时的提前批,属于单独命题,根据分数录取。 毕业之际,老K还被评为了全县优秀学生班干部,在县里面考试时享受了加10分的“特殊待遇”,一个班大概就1个名额,而这10分对于老K实际上是多余的,他后来的分数线远超县重点高中几十分。但这10分,对于其他同学或许就是救命分数,不知道可以改变多少同学的命运,有的可能就差那么1、2分就可以上县重点高中。印象中仿佛还朴素的寻思,当时这些分数为什么不给那些成绩一般的同学。 高中阶段,在全市6个县市万人口的优秀子女PK竞技的大熔炉中,老K表现平平,尽管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始终处于中游,偶尔冲进第一梯队。高考临门一脚,得益于高校扩招的利好,以及全校升学率的抬高,勉强上了一所二本。那时候全省二本录取分数线是左右,老K当年考了分,这个数字倒是很吉利,但离重本还是差了34分。 那一年,同班的不少同学都感觉没有发挥好,一些考上了二本的,一本没上线的,都准备复习了。老K也很苦闷,感觉心有不甘,也加入了复习班的大军。复习那个滋味还真不好受,苦熬了一周,感觉复习压力太大,后来,来自各个方面的,包括老师以及父母都在劝说,老K还是没有抗住压力,选择了不再复习,大家包括老K自己都担心第二年也发挥不好。 于是,就这样,本来是一件喜事,经过这么一折腾,老K以及父母也都平和了很多。 尽管如此,老K还是以整个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是整个院落里面的第一个大学生的名义,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走进了中部某省的省会,开启了四年的大学生涯。在整个家族中,就五舅是一个高中生,爸妈小学没有毕业,勉强读过几册书,连写自己的名字都十分费力,尤其刻骨铭心的是,妈妈每次记电话号码的时候,都要说上好几遍,并且是一个一个数字说,姐姐当时读不进而弃学、小学没有毕业。 老K的人生,也因此而发生了改变!正是由于上了大学,才有后来的考试进入政府系统,成为一枚小公务员,算是初步实现父亲所言:把农壳壳脱了。如果没有当初的读书,自然也就没有后面的事了。梳理儿时的小伙伴、不同层次的同学的际遇,各有各的成长,各有各的归属。大致有这么一些情况。 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为读了书的,上了大学(大专)的,毕业后大多数选择了留在大中城市,开始在城市里熬煎。 一类为没有继续读书的,初中或者高中没毕业的,这里面又分为几种情况。有的机遇好、头脑灵活的,通过积累,也慢慢在地级市或者县级市扎下了根,剩下的,不少开始那10年或者15年,通过南下广州、深圳、福建,或北上新疆、青海、西藏,打工积攒下一些钱,有的咬着牙,在房价未大涨以前,买了房,逐步也留在了城市,而一部分或者相当一部分,感觉异乡城市难以融入,起初没有买房的意识,等到有了想买房的想法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勉强可以付个首付的省吃俭用的存款,在高房价面前已无能为力了,只得转身回到自己的县城,好一点的在地级市,咬着牙把房子首付给付了,也有的选择在所在的乡镇上把房子买下,也有的干脆就回农村,推翻原有的宅基地,自己修了一栋房。 也有极少数迫于无奈,开发身体资源,用身体赚钱。邻村的一个女孩,还干起了骗婚的交易。也有很大一部分男同学,则是子承父志,跟随父母或者亲友,跑线路、上工地,到东南沿海进厂做工。一个高中同学,后来居然成了西南“狗王”,整个川渝地区的大小土狗,都被他以及他的打狗队,毒害了个差不多了,后来因为交易藏獒而锒铛入狱。而更多的人,或许正如“一诗一文每日原创”所述:回不去的故乡,融不进的城市,若是生活如意,谁愿颠沛流离。 在社会阶层日益固化的背景下,读书,或许是泥腿子逆袭的仅有的几条途径之一。 《决策》曾刊文《为什么民工的孩子还是民工?》提到,不读书,则极容易陷入恶性循环,沿袭父母辈的老路,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而在广大农村,父子两代都是农民工的家庭是很普遍的。生活和就业处在一种非常狭窄的状态。生活上重复周围的人、前辈们的轨迹,草率的结婚、早早生养孩子、把孩子丢在老家,自己再出去打工。攒了钱回老家盖房子,或者在乡镇上、县里面买房子,为的是给自己的孩子娶妻生子。孩子们长大了,如果没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很可能继续沿袭这条老路,再度以农民工的身份出去打工... 显然,随着教育程度的不同,安家落户地的差异,各自的人生轨迹也就有了分化。但这有又谁能说得清楚,谁优谁劣呢?大中城市里面的概叹高房价、子女就学、复杂的人际关系带来的痛楚,在县城或者农村的,又羡慕大中城市的教育、医疗、配套设施... 真可谓各有各的世界,各有各的苦乐,人人痛在心,家家经难念,条条蛇咬人。正如路遥《平凡的世界》所言: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 最后,用中国青年网的一篇文章与大家共勉。 人,一辈子有四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次是含着金钥匙出生;一次是读过好学校找个好工作;一次是通过婚姻来改变;如果以上三次都没有了,那你还有一次唯一的机会,那就是靠自己。只能靠自己,一切靠自己。请记住,你读过的书,吃过的苦,都会铺成你脚下的路,带你去想去的地方。自己的路自己走,无论是苦是累,甚至是失败,都要去承担,只要是自己的选择,就要无怨无悔。给自己时间,不要焦急,一步一步来,一日一日过,请相信生命的韧性是惊人的,跟自己向上的心去合作,不要放弃对自己的爱护。 来源干部早读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zhangzx.com/xzyw/13734.html
- 上一篇文章: 跟党走,是我们坚定的选择访藏东英
- 下一篇文章: 访十八军老战士巴桑农奴娃成长记金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