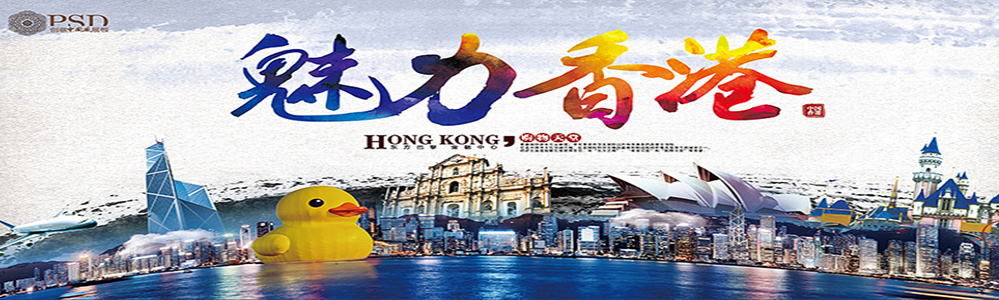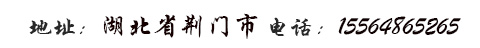王海兵丨汉番之间明代川西北边地的卫所关堡
|
汉番之间:明代川西北边地的卫所关堡 王海兵/北方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提要:川西北边地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民族南来北往、交流沟通的廊道地带。明代川西北卫所关堡的通道性质非常显著,维持松潘南路和东路的畅通是明代在川西北边地统治的关键。卫所关堡与川西北边地族群的互动频繁而深刻,边地族群对通道沿线关堡的袭扰,在更多的时候表现为生计性的劫掠或索取,这本质上是由川西北特殊的地理环境、边地族群的生存境况以及当地汉、“番”力量的消长决定的。川西北边地卫所具有土汉混编、军政兼辖的特点,经过明朝的长期经略,卫所关堡体系在民族关系调控、道路拓修、区域市场建构、人口迁徙、“教化”施行等方面促进了川西北边地社会的发展变迁。 关键词:明代;川西北边地;卫所关堡;族际互动;社会变迁 明代在川西北边地设置了以松潘卫为核心的防御体系,同时沿着河谷通道和一些重要的交通要道修筑了大量关堡,这些卫所关堡与边地社会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对于明代川西北卫所的研究,既有的成果更多地侧重从中央政府对藏区治理的视角进行探讨,内容涉及明朝在川西北地区的政治统治、交通、移民、屯垦等方面。近年来,亦有学者注意到了川西北卫所与藏羌民族之间的族际互动。[1]本文以明代川西北边地卫所关堡军政功能的发挥为切入点,着重考察卫所关堡与边地社会的互动以及由此所引发的边地社会的发展变迁。 一、镇戍与管控:明代川西北卫所体系的设置 明朝初年,明军乘威、茂等处“土酋”反叛之机,挥师川西北,平定其地,先后设威州守御千户所、茂州卫指挥使司(在州治东)。叠溪守御千户所在茂州卫北,洪武二十五年()由茂州卫改隶四川都司,领长官司二,其中长宁安抚司在正统八年()改隶茂州卫。洪武十二年(),“平羌将军”丁玉率师分别沿岷江上游及青川驿道平定松潘,置松州卫指挥使司,设官领军镇守。洪武二十年(),改松州、潘州二卫为松潘等处军民指挥使司。在平定宣德初年松潘“番乱”后,为了加强对茂州地区以及松潘卫以东涪江上游的防御,明朝于宣德四年()增设松潘卫前千户所、茂州卫前千户所、右千户所、松潘卫小河千户所,分别调利州卫前所、成都中卫左所、宁川卫后所、成都前卫后所官军实之;设溪子、叶堂、松林、三路口4驿站。[2](P.)松、茂等边卫由四川其他地方之卫所官军分遣,实行轮戍制度。龙州为“夷夏之噤喉,蜀川之扞蔽”[3]。洪武四年(),龙州薛文胜归附明朝,其属部李仁广、王祥因输送粮饷有功,亦得世袭。洪武十四年(),明政府在龙州置松潘等处安抚司,以薛文胜为安抚使,洪武二十年()改为龙州,洪武二十四年()又改为龙州军民千户所,旋复为龙州,州治亦自青川移设乐平镇。宣德九年(),明朝升龙州为龙州宣抚司,以土知州薛忠义为宣抚使,州同李爵为副使,州判王玺为佥事。龙州宣抚司隶属于安绵兵备道,其主要职能为“控制诸番、保护内地”。龙州原有土官3员,各分地方管辖。嘉靖年间,宣抚使薛兆干、副使李蕃“分领西南白草一带番夷”;佥事王枋“分领东北白马一带番夷”,两处“地方数百里,所统番、汉无虑数万众”。[4](P.)安绵兵备道驻扎绵州,境内无卫所建置,所属州县有利州、保宁、青川等。安绵兵备道的主要防守职能为,“东备汉沔之盗、西备白草之番”,其辖区内的睢水“提督地方十三关堡,坐落安、绵二县地方,所以防御茂州三长官司、天池、大坝诸番”。[4](P.) 松潘、威茂、安绵构成了明代川西北边地的三大重点防守区域。明政府依托卫所、城镇,在三大防区的地势紧要之处及交通要道沿线设置了大量的关堡、墩台,并派兵戍守。松潘防区以松潘卫城为中心,东至小河千户所,再至龙州宣抚司,南抵叠溪界,北至漳腊屯堡,总计各路关堡及墩台共87处,戍守主客官军、舍余、游兵共名,每年额定松潘等16仓粮米共石。茂州、叠溪、威州防区以茂州卫城为中心,北抵叠溪千户所,再由叠溪北行至松潘界,自茂州小东路抵安绵界,自茂州南路抵威州千户所,再由威州至汶川堡、彻底关,抵灌县界,自威州西路抵保县堡,以上威、茂、叠各路关堡、墩台共处,戍守主客官军、兵快、“羌番”共名,每年额定广备等24仓粮米共石。安绵防区设守备指挥1员,驻石泉县,提督指挥4员,分督所属各路关堡共25处,戍守官军、兵快共名,每年额定大印等仓粮米共石。[5]明朝川西北边地关堡、墩台亦随着边防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增置、废弃或改名,其中茂州卫辖区关堡、墩台的设置主要集中在洪武、成化及嘉靖年间。[6]在松潘卫防区,为了应对西北部蒙古人的威胁,嘉靖二十年(),巡抚都御史刘大谟等奏请在松潘北部漳腊等地增加官军名,展修漳腊城堡,建置官厅、营房、神宇等,并修筑边墙丈,深挖坎井口。[5] 在作为国家力量的卫所嵌入到川西北边地社会的过程中,一些当地的族群势力亦被吸纳到了卫所体制之中,形成了土汉官混编参用的格局。在川西北藏羌族群聚居之地,明朝封授了诸多安抚司、长官司,以作为卫所统治的藩篱。安抚司、长官司之下,每寨立牌头、寨首。松潘等处军民指挥使司领有17个长官司和4个安抚司,其中阿昔洞等13个长官司设于洪武十四年(),其余的均设于宣德、正统年间(–)。安抚司安抚及长官司长官有的以寨首升任,也有以喇嘛为之者。土官系统应承担纳租赋、服徭役等义务。洪武十六年(),明廷规定,“西番之民……宜计其地之多寡以出赋。如三千户则三户共出马一匹,四千户则四户共出马一匹,定为土赋”[2](P.62)。松潘等处安抚司、长官司“宜以其户口之数,量其民力,岁令纳马置驿,而籍其民充驿夫,以供徭役”[2](P.63-64)。此外,土官属下的土兵亦是边地卫所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服从卫所的指挥与调遣。 明代川西北边地的族群边界及族群间的认同复杂多变。正统六年(),鸿胪寺通事序班祁全奏言:“臣先奉命往四川勘事,切见松潘等处祁命等簇寨番人杂处,有大姓、小姓之分,僧教、道教之别。如国师商巴罗只儿监藏等此道教为小姓,禅师绰领等此僧教为大姓。各有管摄,不相干预。近年以来,商巴因与离叭剌麻争夺境土,纠集番众,互相讎杀,乘机虏掠军民孳畜,以致边境不宁,动扰兵众,深为未便。今商巴及绰领见在京师,乞各授敕一道,令照族姓分守地方,钤束番人,毋相侵犯,庶几蛮夷知警,边方宁谧”。[2](P.)祁全的调查报告揭示了川西北藏羌社会中“族姓”与宗教之间的密切联系,但是宗教信仰并不是区分大小族姓的根本依据,宗教往往具有跨族姓的影响力。[7]鉴于“番僧”、喇嘛等在调解寨落间纠纷、充当边地向导、收集边地情报、引导“番民”向化等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明朝于宣德六年()在松潘地区设僧纲司,置都纲、副都纲各1员,并许以在本地建寺的权力。此外,明朝还在川西北边地封授了国师、禅师等。这些宗教势力与当地土官系统共同处理寨落的内部事务,构成了明朝统治川西北边地社会的重要支柱。 二、明代川西北边地族群对关堡的袭扰 就岷江上游的整体防御形势而言,“松、茂、威、叠大势如一身然,松潘首也,叠溪项与喉也,茂州腹也,东之土门,西之威与汶、保,其手足也”。[8]其中,松潘则为“诸番之要区,东连龙、安,南接威、茂,北抵胡虏,西尽吐蕃,西北又与洮、岷连壤,镇城衙门、关堡之外,四面皆番,故经略者谓蜀之各镇惟松潘纯乎边者也”[5]。因特殊之地理位置及民族分布格局,在与边地族群的互动中,松潘以南的松茂道沿线关堡显得尤为突出。 自宣德年间开始,“番人”对松潘南路关堡的劫掠逐渐增多。正统九年(),为防堵松潘南先结沟等处“番人”,巡按四川监察御史陈员韬等奏请设立平夷、靖夷、普安3堡,各拨官军人守之,“半岁一更”。[2](P.)上述关堡位于松潘至叠溪守御千户所的松叠道沿线。此外,当时在叠溪以南、茂州以北的黑虎等寨“番蛮”亦“累次聚众攻围松溪、椒园等关堡”,杀掳军民。[2](P.)针对松潘南道频繁发生“番人”对关堡的攻击,正统十一年(),明朝政府命四川都指挥佥事徐贵、郭礼、孙敬提督官军,分守松潘至茂州一线地方,并划定责任区段:徐贵自西宁关至平夷堡,郭礼自金瓶崖至靖夷堡,孙敬自永镇堡至新堡,俱听镇守都指挥佥事王杲等调遣。[2](P.)总体来看,在成化之前,“番众”虽屡次攻击关堡,但明朝的川西北防线尚未遭到很大破坏,且兵力的调度、关堡的增修亦甚有条理。至成化年间,川西北边地形势愈加复杂,松茂道沿线关堡时常遭到劫掠。镇守松潘等处副总兵署都指挥同知尧彧奏言,“松潘至叠溪、威、茂卫所,山峻路狭,东西千余寨,寨数百人,累抚累叛。近愈猖獗,谋欲斫关攻堡,时出劫掠村落,阻塞运道”。[2](P.)除了松茂道沿线外,岷江以东及龙州一带的白草坝等“诸番”亦构成了这一时期川西北边防的重要威胁。成化四年(),松、茂各城军士调征都掌,边地关隘多失巡守,白草坝等“番众”遂乘虚“屡寇安县辕门坝、石泉县大方关等处,焚庐舍,杀掠男妇二百余人,钱谷、牛马无算”,[2](P.)甚至还攻劫龙州、江油等地。龙州境内的白马路等“番簇”亦聚众攻围关堡,阻塞粮道。面对川西北边地的乱局,自成化十三年()开始,明政府调遣汉、土官兵人于松潘东、南二路分进,在松茂大道、涪江上游及其支流白草河等地展开清剿。至成化十四年(),明军攻破白草坝、西坡、禅定、曲山诸大寨,总计“前后破灭夷寇五十二寨,招纳降夷一百五寨”[2](P.)。成化十八年(),明政府于川西北边地增设协守参将,加强对松潘东路自小河直抵龙州、安、绵、石泉等地的防御。 事实上,明代川西北地区“番乱”的频发与边地官员对“番务”的处理不当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朝初年,明政府在川西北边地“或兴师征讨,或宿兵防备,所遣皆重臣名将”[2](P.)。自宣德以后,松茂地区官军为“番人”所信服者渐少,由于“任用非人,抚御失宜”,致使明朝初年所封之安抚司、长官司等“熟番多畔[叛]”[2](P.)。在宣德二、三年间(-)以及正统四年()所发生的规模较大的“番人”起事中,其起因皆为当地镇守官员的处理不当,而不是“番人”有意为之。明代戍守松潘之官军在边务问题上主张以武力从事者居多,以文德抚边者实少。对此,杨廷和指出,“夫羌地刚卤,不生谷粟,时出鼠窃,以自全活,固无他异图也。先是,为将者,欲以多杀人,贪天之宠。每因其来会盟时,醉之以酒,尽杀之,无一得脱者,其父子兄弟怨入骨髓,兵连祸结,将无已时于乎”。[4](P.) 同时,川西北边地险峻的自然环境以及卫所军士对山川形势的隔膜,对明朝在当地统治的深入造成了阻碍,并在客观上助长了“番人”的劫掠。胡世宁云,“大抵番虽强恶,而种类各分,每寨多者不过千人,少者不过数十,其势不相统一,其情虽贪利好杀,而犹尚信可驭也。惟其山高地势险甚,而吾人少入其中,不能知其地利”。[4](P.)申时行亦指出了川西北地理环境对用兵造成的影响。松、叠、茂地方“重山复岭,深崖密箐,自来蕃人出没,种类实繁。本朝置戍屯兵,稍示禁制羁縻之意,然山谷险远,粮运艰难,番人聚如蜂蚁,散如鸟兽,我兵追逐,则彼深藏远伏,不可穷搜,我兵罢归,则彼倏至突来,不可禁遏”。[4](P.)万历年间,徐元太云,“番之敢于蔑视堡军,而朘此脂膏,啖此血肉,稍不如意,复从而毙之者,岂独强哉,亦恃此险固,知我之无奈彼何也。我军之过于畏视番蛮,而割肌以充,沥髓以润,苟得全躯,即忻然忍痛者,岂本弱哉,亦怵此险固,知彼之非我可图也”。[4](P.)又因不习地势,川西北卫所军士之作战效能往往不及当地的土兵、乡勇。边地“番夷所畏者惟土兵,知客兵难以久留,且不识其地之险易,虽多不畏”[2](P.)。嘉靖年间,四川廵抚张时彻云:“兵贵乡导,取其明地利也。川中之兵,军快不如土兵,土兵不如乡勇。葢生长山谷,胆气既粗,逼近番寨,习尚略同,数经战阵,进退亦利。故前此官军一千,不能敌百余之番,而坝底五十乡勇,乃能冲锋破敌,其强弱可知也。”[4](P.-) 此外,边地卫所军士生活的窘迫亦影响到了关堡防御的实施。宣德以后,川西北边地驻军时常面临温饱问题。宣德十年(1),据松潘总兵官蒋贵奏称,其“所统皆极边之地,军士月粮减少,日用不给”。为提高兵丁待遇,经行在户部讨论,“定拟松潘军验口支给,小河、叠溪、威、茂二州四卫所马军一石,步军有妻小者七斗,无者五斗”。[2](P.-)正统四年(),四川按察司佥事王迪、镇守松潘都指挥使赵得奏云,“洪武中,松潘等卫每军岁给绵布三疋、绵花三斤,令自制袢袄。宣德二年,因番人作耗,尽数折钞;七年以后,折半支给,军士艰难。乞命四川布政司仍如洪武中例全给,使皆足以御寒”。行在户部认为此事“宜如盐井等卫,三年一次给赏”。[2](P.)但边地军士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观。据提督松潘兵备右佥都御史寇深言,“松潘、叠溪二卫所地临极边,军士艰窘,难以责其效力,请不分人口多寡,月粮俱给一石”。[2](P.)而户部认为“若再添支,诚恐供运益艰。请已支一石并八斗者如旧,七斗以下俱添至八斗”。[2](P.)景泰二年(),镇守松潘刑部左侍郎罗绮奏称,“松潘极边苦寒之地,守备军士连年无人更代,衣食艰窘,面无人色,实为可矜”。[2](P.)弘治年间,因松茂道粮运阻断,边地卫所关堡驻军生活更显窘迫。弘治十八年(),据工科给事中张文等奏,“南路官军在堡一年,为蛮虐苦,而每月银米又大半尅减,为赏蛮买路之数,是食尚不足,而欲望其竭力御敌,难矣”。[2](P.) 三、川西北边地族群与关堡的生计性互动 维持四川盆地通往川西北边地道路之畅通是明朝在该地统治的关键。边地卫所体制建立后,明朝政府采取纳米赎罪、纳粮中盐[2](P.)、茶课折色以及组织成都诸府州县百姓和当地军士运送等措施来保障卫所关堡的粮饷补给。松潘卫城“深居番境,外则东通任昌、蜡梅,南林[邻]董卜韩胡,西连乌思藏界,北接羊峒、洮州;中则大、小二姓寨簇部落弥满山林,环据险固。而东、南两路一线相通,我军关堡连络参杂”[2](P.)。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明代川西北卫所关堡的通道性质十分明显。明朝初年,明政府在川西北边地“置官军严备,番蛮不敢为非”[2](P.),但自宣德以后,边地族群聚众截路、杀伤运夫、抢掠粮布的事件屡有发生。至弘治年间,川西北边地的道路通行逐渐变得困难。 密布于关堡沿线坚固的寨落碉房为“番人”劫掠提供了便利条件。当粮夫经行其境时,“番人”则“据险装塘,或隔河发冷箭,或临高擂石、截军索货”。[9]而每遇粮运被截,官军“往往剋减军粮,置办酒食、布疋,犒劳买路,而后得进。其守备等官不能宣布朝廷威德,抚驭无方,以致番人轻视,聚众劫掠军民,攻围关堡”[2](P.)。尤其在明军“自牛尾巴失利之后,每岁饷夫、戍卒须南行者,多具银货买路方行。稍不满欲,擂石一下,立为虀粉,故蜀人号南路为死亡城”[2](P.)。松潘南路关堡沿线之族群“见堡爨烟起,即蚁聚而攒食之,军士每忍饥而死,谓之和番,官亦不禁”[9]。据王廷相称,“近年以来,备御关堡官军被害尤甚,方其来也,或据险要遮,或临高擂石,以索财货,谓之买路。及其至也,则日就关堡需求酒食,逼取人事,谓之和蕃。又有债负、年例、人命、痘疮、走失等项银两,取之不得,则执当军士,与之佣工,因而不能归者众矣”。[4](P.)明朝中后期,松潘卫城东南方向的丢骨、人荒、没舌三寨时常扰乱南路及东路,“跳梁架嘴,阻截粮运,时或默地装塘,劫掠财物,如戍军之轮边有新班钱、架梁钱、放狗钱、躧草钱,索取无厌,彼番之来堡有下马酒、上马酒、解渴酒、过堡酒,吞噬多端”[9]。此外,松潘东路亦存在类似情况。弘治十年(),巡按四川监察御史荣华奏言,“比者番人据险,南路不通;其东路往来者,必用钱买路。守备诸军往往为番人种田。田功毕,复追偿所食过粟,又每肆劫掠,军士以是疲困。巡抚官以用威慑为启衅,遂专务持重,不事巡理。幕府月取军粮买酒、布与番人,名曰赏番,其实买和也”。[2](P.)但总体而言,东路“道路颇宽,番寨稍远,间有出没,我军犹可为备”[2](P.)。 正德十六年(),据威茂兵备副使吴希由查报,“叠溪年例赏番,该银四千九百余两,官惟给银一千二百余两,余皆军办,即此可例其余也”。[4](P.)鉴于此,巡抚四川都御史胡世宁建议“赏番银”由政府统一给予,“召各番寨首,令其各报所统番人名数,与之定约,每岁赏例,番首若干,众番若干,或岁或时,皆有常数,要在比前总筭稍优,以慰其心,其熟番为我守保[堡]送粮者,尤当加厚,或给口粮,或倍常赏,慎不负其劳、失其心而使怨畔[叛]。至于平日索要官军接遏、过午、送路等酒,过觜、买路、过班等钱,一皆禁革,不许番人私索于军,亦不许军人私送于番”。[4](P.)胡世宁对松潘南路粮道不通的原因作了如下分析:“弘治年间,承平日久,都御史潘蕃等廵抚惟以保守为事,以欺隐为能,军杀一番,则坐以擅杀激变之罪。番杀一军,则坐以玩寇失机之罪。由是,官军垂首丧气而惟扣粮闭口以赂番,或弃其兵械而执农器以为番役矣。由是,番人得志,日渐骄横,每年班军累死、饿死、杀死者十常八九,而道途任其邀刼,关堡任其残破,一皆付之不知。边堡有报,则阴中以法,问其来使而实言有警,则按以大杖,而使之几死。后有问焉,则大声对众而答言无事矣。不幸而事闻朝廷,则隐匿之罪,仍付之下吏,曰彼不曾呈报也。此前人之善为保守,而坐制部台,称为老成也。此南路之所由以塞,而惟东路仅通也”。[4](P.-) 由上文可见,明代川西北边地族群与关堡的互动频繁而深刻。边地族群对卫所关堡的袭扰,在更多的时候表现为一种生计性的劫掠或索取,这本质上是由川西北特殊的地理环境、边地族群的生存境况以及当地汉、“番”力量的消长决定的。 为了疏通道路、解决粮运困难问题,明朝官员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对策,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加强对松茂道的整饬,以化解“番人”据险为乱。正德元年(),巡抚四川右副都御史刘洪奏言,“松潘至茂州三百里,山觜险恶,一蛮掷石,百人不能过也。且其路随河曲折,蛮下山抢掠为易。前副总兵姚彧尝削其坡陀为陡坎以制之,而今渐平夷矣。又,小东路一带,偏桥陡峻,人马时坠而没焉。宜凿其未通山觜,如彧法,刬削其坡辟路,令广立桥。今固险阻既去,夷无所恃矣”。[2](P.)其二,修葺关堡营房。“松、叠、茂所辖关堡城垣多卑坏,营房多倾圯,宜委官查勘,循次修理,务坚实可久,以壮边方之观”[2](P.)。其三,加强对通事的管控。官军应“严敕通事不许通番、借钱及伪立军人借番银两文约,无主名者,不许代还。如番据险横索,究该管通事交通之情,如律重治”[2](P.)。其四,加强对沿线“番寨”的管理。正德四年(),四川守臣奏云,松潘“南路由灌县而入,以溯叠溪,地势险隘,番寨相联,粮夫经行,多被剽掠,不惟边人告病,而内地亦困。自洪武、永乐以来,虽迭用大兵,终请平而罢。今各寨颇知向化,而南路之防为急。欲令每寨择其众所信服者,立为牌头、老人名色,就令管束诸蛮。凡遇粮夫、使客、商贾经行并官军送哨往还,各会同番僧剌麻,官军逐程护送。朔望赴所辖卫所,听参将、兵备官查审用命不用命,量给茶、酒、布匹,以抚恤之。庶或因事捄弊,而道路可通矣”[2](P.)。 四、卫所关堡与川西北边地社会的历史变迁 (一)松潘东路“白草番”等地的就抚。“白草番”为龙州李氏土官所管辖,该地在龙州西南,东抵石泉,西抵南路“生番”,南抵“茂州番”,北抵平武县境。“上下白草凡十八寨,部曲素强,恃其险阻,往往剽夺为患”。[10]嘉靖十三年(),巡抚都御使宋沧克平坝底、白草诸寨,“诸夷献侵地二千余顷”。[9]嘉靖二十四年(),白草等18寨“番蛮”聚众于羊甬、白泥一带劫掠,攻克平番、奠酒二关,截占漩平,以阻石泉兵粮之路。[5]嘉靖二十五年(),明朝派兵名,“一由龙州,一由石泉,一由霸底,所斩获甚多,事平,增双溪、大鱼、永平、奠边诸堡,革抚赏,断盐茶,予以白旗,永塞入龙之路”。[10]嘉靖二十六年(),四川巡抚张时彻会同何卿再次进攻“白草番”地区,“克营寨四十七,毁碉房四千八百,获马牛器械储积无算”。[11](P.)经此一役,“白草番”头目“埋奴砍狗,对天盟誓,永为白人”,并“退还石泉县土地,河东自走马岭迤南锐子坪起,河西自木门架起至枇杷岭止,又自射溪沟起一带至永平堡止,俱还石泉县乡民耕种”。[4](P.)为此,张时彻奏请将“白草番”地区18寨“遗番各立牌头,给以牌面,开写本寨群番姓名,务要各安生业、认守地方,……先年牌头月粮与岁给赏需通行革去。各番但有出境为盗者,酋长举报掌堡等官,量治以法。若酋长有谋为不轨者,许各寨报官擒捕,则黑、白自分,可免连累之患矣”。[4](P.)在明军的武力征伐下,万历七年(),石泉县辖境内风村等11个寨的“熟番”投诚。另据石泉县提督指挥刘泽远呈报,白草等17寨民众“亦出马甲、器械投降,愿做百姓,望赏白旗,认守地方”。上述28寨男妇共口,俱更换姓名,且于万寿圣节之时,行叩头之礼,每寨输黄蜡1斤以作灌烛之用,并责令“听我调用,习我汉仪”。[9]明政府亦“许其畜发、顶巾,送子读书,习学华语”,成为编氓。[10] (二)松潘南路附近寨落的抚定。嘉靖五年(),明廷命都督佥事何卿镇守松潘。在何卿任职期间,虽屡有“番人”作乱,但由于治理得法,“终嘉靖世,松潘镇号得人,边境安堵焉”。[11](P.-)万历初年,据四川总兵官李应祥称,丢骨、没舌、人荒、蜈蚣等寨历年来杀死守堡官军、商民等共余人,大小粟谷、列柯、歪地、牛尾等寨“番蛮”杀死军兵等余人。[4](P.)这些寨落大致位于松潘至叠溪的岷江两岸,其中尤以丟骨、没舌、人荒三寨最为桀骜,连年杀害安化、归化等关堡旗军,并劫掠松潘东、南两路军粮,“狼贪无厌,虎噬为王,出没靡常,纵横日甚,数十年来,地方苦其荼毒,莫敢一问者,盖以负山箐之险,挟羽翼之众故耳”。[9]万历七年(),明军围攻三寨之地,三寨牌头人等率众投降,松潘兵备副使杨一桂将不合常例之赏需悉行裁革。此次征剿意义非凡,“廓清数十年跳梁之丑虏,扫除千万里煽焰之妖氛,诸寨畏威,群夷破胆”。[9]万历十四年(),明军再次对松叠道附近为恶之“番寨”采取军事行动,进一步缓和了松潘东南部的局势。 (三)龙州宣抚司地区的改土归流。至明朝后期,由于时代之变迁,龙州土司越来越难以起到防卫边地之作用。据张时彻言,龙州土官“今乃弃弓马之习,而恬于膏梁,婚缙绅之门而恃其庇覆,以沉湎为生涯,用奸人为羽翼,纵恣不法,干没为奸。无事则卖土兵以纳役钱,有事则盗军饷以充囊橐。号令则偃蹇不从,提究则赃藏不出。武备日以废弛,番夷渐至猖獗。如此不已,后患何极。议者每欲添设流官,又以事体重大而止”。[4](P.)嘉靖四十四年(),因宣抚薛兆乾与副使李蕃“相讐讦,兆乾率众围执蕃父子,欧杀之”,后又“胁土官佥事王烨,不从,屠其家,居民被焚掠者无算”。嘉靖四十五年(),明军将薛兆乾诛杀,“籍其家,母陈氏及其党二十二人皆以同谋论斩”。[2](P.)鉴于此,巡抚谭纶建议明廷在龙州宣抚司地区“创建府治,改设流官”。其原设宣抚司副使、佥事改衔通判,“俱世袭,令辖生熟番夷,不得与有司政事。土民散处宁羌、利、保等处者,悉入版图。且割保宁、成都二府所属江油、石泉二县并青川所隶之,而总隶于川西安绵道”。[12](P.) (四)卫所关堡促进了川西北边地商品流通和区域市场的建构。宣德四年(),据行在锦衣卫指挥佥事何敏言:“近来,卫所官旗多纵家属在堡居住,与番人往来交易,及募通晓汉语番人代其守堡,而已则潜往四川什邡、汉州诸处贩鬻,经年不回,致番蛮窥伺,乘虗作耗,烧毁关堡,劫虏人财。今虽降附,亦宜榜谕诸处贩鬻者各还营堡,仍依宁夏官军更替备御,庶番蛮畏服,边卫宁妥”。[2](P.)另据四川廵抚张时彻称,川西北边地“各番巢穴逼近民居,非有长城远塞之限,往来交易,从古为然”[4](P.)。同时,由于“番中绝无盐布茶米,仰给于我,因掌堡等官防禁不严,以致入堡交易,引惹边衅。今各番降附,听于三路大堡之外空便地方,随其土俗,两平交易,仍严加禁约,如有强买番货,高低价值,又擅入番寨,或纵容入堡贸易者,坐以勾引边衅,从重追究”。[4](P.)由此可见,川西北边地的卫所关堡不仅是军事防御设施,也是当地集市贸易的重要节点。 (五)卫所关堡移民与川西北边地族群的“内地化”趋势。按照洪武七年()定制,大致以人为1卫,每卫设5千户所,1人为1千户所,人为1百户所。川西北卫所属于边卫性质,其军额往往大于腹里卫所。因此,戍守在川西北边地卫所的军士及其舍余的数量相当庞大。这些军事性移民(包括相当数量的回民)的定居点与卫所关堡的分布基本一致。经过卫所关堡的长期经略和汉、“番”间的频繁互动,川西北边地社会逐渐呈现出了“内地化”的趋势。其中,在松潘卫地区,藏羌民众“渐染教化,粗识汉言”。[13]叠溪守御千户所一些寨落的民众“近渐染声教,习尚衣冠”。[13]而松潘南路的茂州“诸蕃”因与汉人“错居”,故“颇知文书”,[4](P.)“教化”程度亦较深。 总之,以松潘卫为核心的川西北卫所是明朝边缘藏区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宣德以后,由于卫所官军在边务问题上处置不当以及军事防御能力衰退等原因,致使“番人”对松潘南路及东路沿线关堡的袭扰活动明显增多。为此,明朝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极力维持四川盆地通往松茂地区道路之畅通。在抚剿兼行、恩威并著的制驭之策影响下,至嘉靖、万历年间,川西北边地“番人”的逐渐向化成为非常显著的社会现象。川西北边地卫所关堡具备军管型政区“辖土治民”的特点,即兼具军事镇戍与地方行政管理之职能。因此,卫所关堡与川西北边地社会之互动是综合的、全方位的。明朝在川西北边地的经营,进一步开拓并巩固了岷江、涪江上游的峡谷通道,促进了边地社会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明清时期边缘藏区的移民、开发与族际互动研究”(10CZS)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1]邹立波.明代川西北的卫所、边政与边地社会[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 [2]《西藏研究》编辑部编.明实录藏族史料[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3]郡县志十[A]//(万历)四川总志(卷14)[Z].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册)[M].济南:齐鲁书社,6. [4](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 [5]经略四[A]//(万历)四川总志(卷22)[Z].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册)[M].济南:齐鲁书社,6. [6]关隘[A]//(道光)茂州志(卷2)[Z].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66辑)[M].成都:巴蜀书社,2. [7]邹立波.明代前期川西北“族姓”、边政与宗教关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5). [8](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32)[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册)[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9]经略三[A]//(万历)四川总志(卷21)[Z].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册)[M].济南:齐鲁书社,6. [10](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33)[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册)[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1](清)张廷玉.明史(卷)[M].北京:中华书局,. [12]明实录·世宗实录(卷)[Z].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上海:上海书店,. [13]郡县志十四[A]//(万历)四川总志(卷18)[Z].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册)[M].济南:齐鲁书社,6.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年10期 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zhangzx.com/xzny/7752.html
- 上一篇文章: 笨笨资讯游西藏,这26个景区6月30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