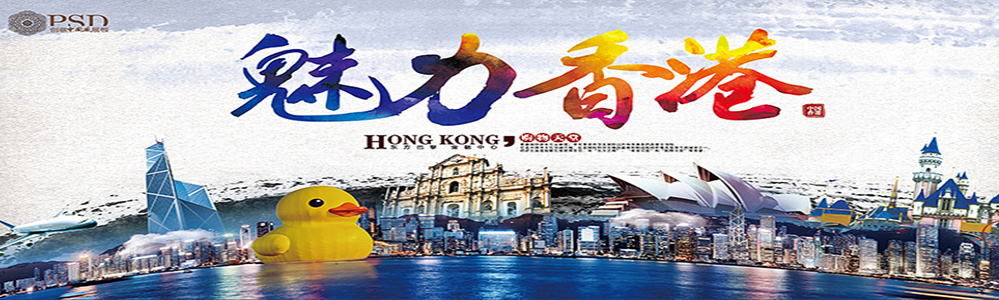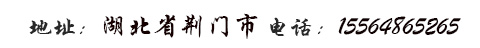真实与想象的西藏关于六世达赖密宗和
|
真实与想象的西藏:关于六世达赖、密宗和“西藏热”——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沈卫荣 宗教与政治 三联生活周刊:从历史上看,藏传佛教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是否激烈? 沈卫荣:他们经常有冲突,实际上有时候也很暴力。年在波恩开过一个讨论西藏神话的会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大意是说现在大家把西藏神话化了,认为西藏佛教徒从来就是非暴力的,一直爱护环境,互相之间友好相处,实际上也不尽然。有人提到西藏的中部藏区,也就是卫藏地区,很早就没有很多木头了,所以当时有些派别之间的冲突的起因就是为了争抢木头,怎么抢呢?我打败你,把你的寺院拆了,木头拿来建我的寺院。还有,格鲁派长期以来受噶玛噶举派的压制,差不多两个世纪一直受压,后来格鲁派联合了蒙古人固始汗的势力,曾经很残酷地镇压过噶玛噶举派,所以都是西藏各教派之间也曾经有过非常激烈的冲突的。 后来因为格鲁派影响太大了,不管是政治,还是宗教,它的影响实在太大,引起了其他教派的不满。到了十八世纪,西藏曾经出现过一个“宗教圆融运动”,又叫“利美运动”、“不分派运动”,这个不分派运动实际上是其他各个小教派联合起来反对格鲁派一家独尊的运动,因为格鲁派太强势了,萨迦派、噶举派、宁玛派还有其他小派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和格鲁派抗衡,所以,西藏各宗教派别之间的冲突是一直有的。从这个角度来讲,说达赖喇嘛从来就是西藏的宗教和政治的领袖是不对的。实际上西藏各个教派都有自己的宗教领袖,宁玛派绝对不会认为达赖喇嘛是他们的宗教领袖,噶举派也不会认为他是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不能代表全西藏,因为西藏有很多不一样的教派。只是现在,达赖喇嘛才变成了西方唯一的西藏认同,所以大家才会说达赖喇嘛是西藏的政教合一的领袖,实际上以前不是这样的。 沈卫荣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宗教的发展其实一直与政治密切相关? 沈卫荣:五世达赖以前,达赖喇嘛并没有任何足以号令全藏政治影响力。后来五世达赖到清朝来朝贡,和中央建立了关系,又得到蒙古固始汗的支持,这样才慢慢兴起,开始有政治影响,在这以前格鲁派一直被噶玛噶举派欺负的。五世达赖喇嘛后,清政府对西藏的控制进一步加紧,六世达赖喇嘛实际上是被清朝皇帝废掉的,害死的。 五世达赖以后,宗教领袖很多是中央政府直接扶植起来的。中央政府支持西藏的某一派是有历史的,最早萨迦派是跟元朝,明朝是噶玛噶举派。到明朝后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影响比较小,三世达赖喇嘛曾经尝试通过蒙古王子俺答汗推介而寻求明朝中央政府的支持,但被当时的宰相张居正拒绝了。后来五世达赖喇嘛可以说是自己找上门来的,他直接和清政府建立了联系。五世达赖喇嘛后来在固始汗的帮助下建立起了个一个西藏地方政府,使得西藏有了一个有效的地方政府机构,而清中央政府对西藏有主导权。 宗教的发展没那么纯粹,宗教里面的斗争都很残酷。内部要靠外部支持,外部也要靠内部来实现对西藏的统治。格鲁派的宗喀巴属于宗教改革派,在宗教上影响力一直很大。达赖喇嘛能做成这么大的一番事业,当然跟他的宗教影响有关系,我们不能说达赖喇嘛完全是清朝皇帝扶植上去的,实际上他们双方是互相借势的。 三联生活周刊: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最近几年非常“红”,历史上真实的他是什么样子? 沈卫荣:他本人是个很可怜的人,二十多岁就死了。他是康熙皇帝、蒙古的拉藏汗和五世达赖的亲信桑结嘉措之间相互斗争的牺牲品。仓央嘉措是桑结嘉措立的,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桑结嘉措15年秘不发丧,康熙皇帝偶然得知消息后,非常生气。为了惩罚桑结嘉措,认为他立的达赖喇嘛不能作数,所以要求把仓央嘉措押解到北京。在押解途中,路过青海他就死了。实际上应该是被害。后来有传说说他失踪了,或是出家了,但是那也都是出于一些不愿意他这么死去的主观愿望胡编的,有人说他辗转到了内蒙古阿拉善,建立了南寺,又变成活佛了,流传了下来。实际上,历史上的达赖喇嘛没几个活到成年的,所以他们转世的频率特别快。从五世开始到后来,只有十三世是真正掌握了政治权力的,这已经是到了民国时期了。在这以前,达赖喇嘛很少长到成年,并真正执掌政治权力的。 一位僧人在大昭寺楼顶点酥油灯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待仓央嘉措情歌的流行? 沈卫荣:这个多半是目前汉人,特别是有小资情调的人想象出来的,多半是我们把自己的情感投入到了所谓的仓央嘉措情歌之中去了。目前流行的一些六世达赖情歌无疑是伪造的。我仔细地读过他的原作,好像一共是63首,从文字到内容都很简单,最初是于道泉先生翻译的。事实上,这些被称为情歌的东西是不是六世达赖喇嘛本人的作品也很难说,在我看来这些诗歌很有可能是民间流行的一些歌谣,它们不像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写出来的。一般藏传佛教上师们的作品都涉佛教义理,文字都极其典雅,而仓央嘉措的情诗都特别平直,就是民间那种直抒胸意的风格,甚至很难把它们称为情诗、情歌什么的。我是读古藏文的,但在仓央嘉措的作品中并没有读出目前大家争相传颂的这些东西。 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人打着仓央嘉措的名义推销那些富有小资色彩的东西,这个现象值得研究。实际上是把我们的梦想,把人类对爱情的追求,把我们对失落了的过去的怀恋,全部都寄托到了六世达赖喇嘛身上。目前大家对六世达赖及其情歌的热爱真的是非常现象级的,非常有意思。 被标签化的密宗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从现在的藏传佛教上还能看出多少印度的影响? 沈卫荣:藏传佛教的最典型的特征是密教,而密教的教法和修行都是从印度传过来的。以前对密教的来源有疑问,很多人说密教可能就是汉地的道教,但这种说法越来越不可信了。后弘期西藏所传的跟密教相关的传承都是印度的,当然西藏对它们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收,因为印度本身的佛教传统到13世纪就没了,而在西藏却一直发展了下来。现在要研究密教,尽管源头是印度的,但研究密教的重心必须在西藏、必须用西藏的文献,因为它们在印度已经消失了,留下的文献也很少。当年大量的东西都是从印度传到西藏,然后在西藏进一步扩展的。 有西方学者认为西藏对世界精神文明的最大的贡献,或许也是唯一的贡献就是密教,如前所述,虽然密教最初是从印度传过来的,但它的发展和流行是在西藏。修密教的人不会去印度,都要去西藏。藏传佛教前弘期是显教,和我们汉传佛教没有特殊的区别,后宏期才传密教。藏传密教形成的地域并不是在现在的西藏,而是整个西域,特别是敦煌那一带。今天西藏佛教文化里面多少是印度的成分,多少是汉地的成分,多少是西藏自己的成分,很难划分。但毫无疑问印度对西藏佛教文化的影响是最深的,所以西藏有些后世的佛教史家甚至都把自己祖先说成是印度人,说成是释迦家族的后裔,这当然只是佛教徒的一种狂热的说辞,并没有任何实际的历史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简单来说,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沈卫荣: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实际上同属于大乘佛教,是大乘佛教的两个不同支派,从根本上来说它们是一致的,只是汉传佛教重显乘,而藏传佛教重密乘。当然,汉地佛教里面也曾有过密教,但按藏传密教徒对密教得四分法来看,汉传密教还是比较基础的。比较高档的密乘修行都只出现于藏传密教中。大家知道,佛教有小乘和大乘的区别,小乘佛教满足于自己的成就,而大乘佛教说的是普度众生。小乘佛教就是你自己修行,得道成佛就是成为罗汉,东南亚佛教比较多这样的。大乘佛教说即使你自己修行不成功,还可以有菩萨来拯救你,你只要每天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念诵观音大悲咒等,到你死的时候还有菩萨会来救你,可以带你去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去享福。大乘佛教说你这一辈子修习佛教就可乘佛,即即身成佛;而小乘佛教徒则至少要修七辈子才能成为罗汉。 密教则更进一步。一般的佛教徒重视的是戒除贪、嗔、痴等所谓三毒,这样就可以成佛,而密教则不一定需要戒除贪、嗔、痴,而是要把贪、嗔、痴作为成佛的道路,成为修行的一种方式,这样可以更快地成佛,密宗的修习是成佛的一条捷径。于是,喝酒、双修等表面上看起来和贪、嗔、痴相关的东西实际上都变成了密教修行的一部分,这是密教和显教的根本性的不同。密教在唐朝的时候在汉地也有过传播,也曾有密教仪轨流传,但后来就失传了,故在汉地并没有真正建立起密教的传统。而藏传佛教接受和发展了印度密教的所有传统,例如,瑜伽女的修法、男女双修等各种属于比较高级的密教修法,只有在藏传佛教里有。这些修法在印度也是到了9世纪左右才比较流行的,而那个时候汉传佛教已经停止从印度输入了,所以汉传佛教中没有这些内容。但这些东西很快也传到了汉地。 历史上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交往很多,只是以前我们不知道。最初是汉传佛教影响了藏传佛教,即文成公主入藏的时候,带去了很多汉传佛教的东西,后来更多的是藏传佛教影响了汉传佛教。汉地密教的修法都是从西藏来的。我们中间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密教,以为密教就是双修,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是被标签化了的密教,我们对它真正的意义、修法可以说完全不了解,还需要启蒙教育。 三联生活周刊:密教实际上是有一套复杂哲学意义的,内容也比较高深,为什么现在会被简单化、猎奇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理或是文化心理? 沈卫荣:这实际上也是很长的一个过程。为什么西藏被神话化、为什么密教被西方人那么快地接受,实际上也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这跟当时的“新时代运动(NewAgeMovement)”很有关系。美国人以前都是新教徒,对性之类的东西非常保守,认为是原罪的来源,后来有人以密教作为思想工具,来对抗这些被认为很伪善的东西,所以从上纪世50年代初就开始写瑜伽、性高潮与革命之类的书,大致在这个背景下,把这些东西传进去了;传进去之后为他们的吸毒、性解放、滥情、滥性,提供了合法化的理论依据。 当时很多喇嘛很受欢迎,最典型的是一位叫仲巴的活佛。这个人从年活到年,来自青海玉树一个很小的寺院,他在国内的时候并不有名,后来去英国牛津大学深造。他太太后来出了本回忆录,翻译成汉文在台湾出版,叫《与上师在一起的日子》,很有意思。他太太是个英国人,是一个没落贵族家的小孩。自己上中学的时候,到了反叛期,不愿意好好读书,就寻找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有人介绍她去见这个活佛。第一次见面,活佛迟到两个小时,本来要说法的,结果轮到他说法的时候就昏倒了,喝醉了不省人事。过了一个月第二次去见他,活佛马上就请她上床双修,这女孩15岁,后来他们俩结了婚,成了大丑闻,整个事情很疯狂。还有,有人把根敦群培的《欲经》翻译成了英文,也说这是藏传佛教的东西,说是让人既可以达到身体的、物质的愉悦,同时又可以达到精神的超脱。实际上,《欲经》本来是一本印度的古书,与藏传佛教毫无关系,讲人生经验,其中有一段讲男女性爱的64种方法。后来西方人把它当成色情书,鼓吹这些东西,把密教与《欲经》混为一谈,并随着后者的畅销而日益受人注目。 藏传佛教的流行与这个有点关系,但也不尽然。包括仲巴活佛,他写了很多惊世骇俗的书,有的写的很好,比如《剖开精神的物质享乐主义》(CuttingthroughSpiritualMaterialism),阐释人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与物质主义的关系,开创了心理治疗的先河。他对西方的问题看得非常清楚,然后用藏传佛教的东西来作为治疗的工具。他将新时代美国人对精神性和宗教的过份执着称为“精神的物质享乐主义”。他用癫狂的行为对这一主义的批判矫枉过正,又使它演变成对精神超越和物质享受同时的狂热追求。如果他只是双修,那就是恶魔了。 “想象的西藏”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西藏现在是被西方人“香格里拉化了”、“精神化了”,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 沈卫荣:年,一位名叫詹姆斯·希尔顿的人写了一部题为《消失的地平线》的小说,讲述的是二战前一架英国使馆派出的飞机被劫持到了一个叫“香格里拉”的地方。詹姆斯·希尔顿在小说里写了很多对“香格里拉”的想象。在乌托邦式的想象下,《失落的地平线》中的香格里拉成为西方白人的伊甸园,实际上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梦寐以求的一个在东方的世外桃园。当然,香格里拉并不是西藏人的乐园,香格里拉的居住分布充分体现了这种平和的神权统治下彻头彻尾的种族等级体系:住得越高,地位就越高,而西藏人除了会微笑以及伺候他人外,似乎就再不会做什么了。总而言之,香格里拉是一座西方文明的博物馆,是18世纪欧洲人对于东方和东方传统文化的幻想,是西方人为自己创造的一个精神家园。 这几年,西藏及藏族文化在西方广受北京看白癜风去哪个医院好北京中医白癜风医学研究院怎么样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zhangzx.com/xzxw/6677.html
- 上一篇文章: 区内法规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